
二战后社会风气转移,奥拉德(Richard Ollard)撰写皮普斯传记(Pepys:A Biography)时遂一改早期海军史家对皮普斯的歌功颂德,开始对其性格的复杂性进行客观分析,并不吝于展示其缺点。该书于 1976 年问世,是距离本书最近的重要传记。1995年托马林发表了一篇对莱瑟姆和马修斯版日记的书评之后,奥拉德给她写了一封信,信中的和善话语最终鼓励托马林写出了这部全新的皮普斯传记。
克莱尔•托马林生于 1933 年,比皮普斯小了整整三百岁,如今年过九旬,正在向期颐之年迈进。她和皮普斯一样是个伦敦人,也和皮普斯一样毕业于剑桥大学,后来担任文学编辑,撰写书评,最终成为职业的传记作家。她给雪莱、简·奥斯丁、狄更斯以及默默无闻的狄更斯的情妇内利•特南都写过传记,都获得了好评。
这部皮普斯传是她晚年的杰作,据托马林自述,她一开始就不打算把写作重点放在皮普斯对海军的贡献上,而是试图还原出一个活生生的皮普斯来。书中第十三章记述1663年11月,皮普斯决定让理发师剪掉自己的头发,并从理发师那儿买了一顶佩鲁基假发。介绍完假发事件的前因后果之后,作者评价道:
假发意味着……你看起来更像个画像,而不是个大活人。这就是为什么假发在肖像画上有如此窒息生命的效果,扼杀了巨大的卷发垫子下面的个性。不幸的是,在皮普斯的所有肖像画里他都戴着假发;你只要看看他同时代的少数几幅不戴假发的肖像画就可以看出他们有多生动:头发斑白的老伊夫林,牛顿的小半身像,稀疏的头发往后梳着,德莱顿的一幅罕见的不戴假发的肖像画。
这段话不经意间透露了托马林的价值取向和写作意图。在她看来,假发作为个人成就和社会地位的标志(symbol)同时也遮蔽了主人的真实个性,而她写作的目的之一无疑就是要摘掉皮普斯的“假发”,展现出他被掩盖在“巨大的卷发垫子下面”的真面目和真性情。这就决定了托马林撰写本书时所使用的最重要的材料是皮普斯的日记而不是海军部的公文档案。她说在日记之后,皮普斯的公文、书信等等都不能看出这个人的样子,只有日记才记录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甚至“比当下更真实”。这也决定了传记各部分的比例安排,全书除序言、尾声外,分为三个部分共二十六章,第一部分1663-1660年有六章,其中第六章题目已为《日记》;第二部分1660-1669年是皮普斯写日记的十年,占了十三章,是全书重心所在;第三部分1669-1703年有七章,讲述皮普斯的后半生。作为对照,前述布莱恩特的皮普斯传记三部曲,从 1663 年皮普斯出生到1669年停写日记,只构成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本书之迥异前贤可见一斑。
皮普斯写日记时正当盛年,精力旺盛,兴趣广泛,日记内容异常丰富,使托马林面临巨大的工作量。书中写道:“皮普斯的日记打从开头起就一下子做了很多事情,让人望而生畏。它列出了去过的地方、遇到的人,但没有解释是什么地方、什么人。”这没有解释的部分,自然就需要托马林做足功课,一一加以解释说明:“它(日记)既提供了他工作中的许多细节,也提供了他日常家居生活的点点滴滴。”工作的细节、日常的点滴,牵涉人物众多,信息庞杂细碎,也需要托马林条分缕析,一一理清头绪,串联起来。例如1662年4月23日皮普斯记录他在朴次茅斯出差时和克拉克医生同榻而眠,所有跳蚤都去咬克拉克,皮普斯则毫发无损。这类轶闻趣事一般人读后很容易就忘却了,托马林却独具慧眼,把它和1665年大瘟疫结合起来,作为皮普斯能免受传染的一个解释,由于跳蚤是瘟疫传播的媒介,所以“他有天然免疫力”。这两件事相隔三年,托马林依然能从草蛇灰线中发现因果关联,这是很高明的手法。
托马林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使她得以充分驾驭日记中的海量信息,加上多年文学编辑生涯练就的好文笔,她很擅长重构历史场景,用戏剧的手法再现皮普斯的人生经历,笔法细密轻盈,字里行间带着淡淡的讽刺,又不乏温柔和体谅。全书开篇就像猛然拉开幕布,把一月里的某个清晨,卧室里夫妇的激烈争吵展现在观众的面前。然后作者不失时机地插入一句冷静的旁白:“这场戏在皮普斯日记的这一页中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天是一六六三年一月九日,星期五。”
受益于作者的生动文笔,读者可以读完这本五百页的巨著而丝毫不觉得烦闷。作者不虚美,不隐恶,对皮普斯的丑陋一面毫不隐讳。例如他从同事波维手中得到丹吉尔司库一职,却拒绝按照协定将灰色收入分给波维,对要求履约的波维恶形恶相,令人生厌。他在英荷战争中的表现毫无英雄气概,照托马林的话说,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福斯塔夫(Falstaff),有时甚至比福斯塔夫更像个小丑、更加无赖。他从战争的采购中牟利,却在《海军白皮书》中把自己粉饰成一个无可指摘的勤奋工作者、令人印象深刻的行政长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皮普斯如此性格行事,或许与他自幼饱受病痛折磨,生命危如朝露不无关系。成年后他冒着生命危险接受了膀胱结石手术。手术没有留下正式记录,托马林查阅了大量原始资料,包括同时代人对膀胱结石手术的详细描述、外科医生的笔记,甚至有译自荷兰语的《膀胱结石精论》等等,准确生动地还原了术前准备、手术过程、术后护理的种种细节,非常精彩。难怪吕大年先生夸托马林“功课做得好”。
在全书第一章,针对皮普斯早年的病痛经历,托马林评论道:
疾病似乎教给了他面对病痛的坚韧——因为没有止痛药——并让他下定决心只要一息尚存就尽力抓住能到手的一切并尽情享受。这一点后面还能看到,他兴高采烈地面对瘟疫之年,死亡无处不在,他却攫取一切可以享受的东西。……他对生命中快乐的贪求被疼痛和恐惧打磨得更加尖锐。
托马林对皮普斯的这一评价,在他此后的人生中不断得到印证。联想到1995年托马林为莱瑟姆和马修斯编辑的十一卷本皮普斯日记所写的书评,题目是《及时行乐》(“Carpe Diem”),她的确从一开始就把握住了皮普斯性格的核心特质。
若问皮普斯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物是谁?托马林大概会毫不犹豫地说:“伊丽莎白,他的妻子。”皮普斯一开始就把婚姻当作生活的中心,他的日记以对婚姻的考虑开始,也以对婚姻的考虑结束。在记日记的九年半里,皮普斯对自己的婚姻描述得如此细致,以至于托马林风趣地说“你可以把这本日记交到火星人手里来给他们解释(婚姻)这一制度及其运作方式”。
1669年日记的停笔,学者大都归因于皮普斯的眼疾。但此后三十四年的余生里皮普斯未曾放弃阅读和写作,还写过两本简短的日记,对此托马林的评价是:这两本日记“没有第一部日记的任何特点。缺少了某种本质性的东西——某种使他产生出珍珠的砂砾”。托马林认为日记停笔后不久就逝世的伊丽莎白就是沙砾之一:
他在感情上和想象上都与她绑定在一起。他与“我的妻子”朝夕相对,而又写下了对她保密的东西,这二者之间的张力显而易见;她在或不在,挑衅与愤怒,一次又一次地触动了他最深的自我。日记的存在离不开他对自己和伊丽莎白密不可分的感觉。
托马林把皮普斯日记的成功,部分地归功于伊丽莎白,同时认为伊丽莎白也是日记无法再度续写的原因之一,这是前所未有的观点,也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从这个大胆的结论还可以看到托马林的另一个写作意图:给皮普斯生命中的重要女性以应有的地位,而这一点恰恰是被以往的皮普斯研究者全然无视的。
托马林秉持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对两性之间的权力关系极为敏感。如前面提到的皮普斯戴假发一事,他在日记中记录了他担心邻居、同事、上司甚至女仆会作何反应。托马林立刻敏锐地指出,他唯独无视了妻子的感受,尽管与他同床共枕的妻子才是受影响最大的人。在《婚姻》一章中,托马林用了很长的篇幅描述了皮普斯厚颜无耻地玩弄众多女性的恶行,他能够得逞无疑是因为他的社会地位和财富远远凌驾于这些可怜的猎物之上。造船厂木工巴格韦尔的太太在丈夫的授意下委身于皮普斯,无辜的女性成了两个男人——托马林称之为“恶棍”——交易的筹码。在皮普斯的婚外情中,惟有女演员尼普太太能够在完全平等的条件下与之交往,托马林总结道“毫无疑问,她的独立源于她能自食其力。”
托马林对皮普斯日记中女性的关注,最终凝结成本书最具特色的一章——《三个简》。三个简中,最重要的是简·伯奇,在日记的第一页她就已出现,是家里那个十五岁的小女仆。简和皮普斯夫妇在同一屋檐下朝夕相处,既尊卑有别又亲密无间,她忍受着繁重的劳作、责骂、殴打以及皮普斯的性骚扰,但她并不怯懦,知道如何为自己抗争,甚至经常以辞职相威胁。也许正因为学会了抵抗霸凌,她和皮普斯的关系反而能够维持长久,直到后者生命的终结。长期的共同生活使得简成了日记中仅次于伊丽莎白的女性人物,皮普斯的笔下“展现了她的温柔、善感、勇敢、倔强、幽默、活泼、努力工作并且工作出色、对母亲和兄弟忠心耿耿、对雇主诚实可靠”,以及“她是如何坚强地忍受他的严厉、不公和一贯的累人”。
在托马林看来,简·伯奇代表着一个人数众多却几乎没被记载、没有自己声音的群体,她们的生活细节几乎没有流传下来。借助散落在皮普斯日记中的零碎记录,托马林拼贴还原出了简·伯奇的人生经历,给后人留下了简的一幅令人倾佩的肖像画。
2003 年,塞缪尔·皮普斯协会召开皮普斯逝世三百周年纪念会,这部传记获得塞缪尔•皮普斯奖,这是该奖的首次颁发。托马林在会上做了演讲,题目是《“小老简”》,这是皮普斯在日记里对简•伯奇的称呼。纵观该协会成立一百多年来的演讲题目(协会成立于皮普斯逝世二百周年的1903年,创始成员包括皮普斯日记的编者惠特里,协会网站有演讲题目列表),几乎都是绕着皮普斯打转,托马林的选择尽显女性学者的勇气。
尼克松说过,“在伟大领袖人物的脚步声中,我们听到历史隆隆的惊雷”。这是不折不扣的传统(男性)英雄史观。托马林的这部书,虽然受制于客观条件,无法对历史上长期被忽略的群体做更详尽的描述,但依然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的历史面貌:那就是在普通小人物,尤其是受到阶级、性别双重压迫的女性小人物——比如“小老简”——的体内,也蕴含着不逊于伟人足底雷声的日升月落、斗转星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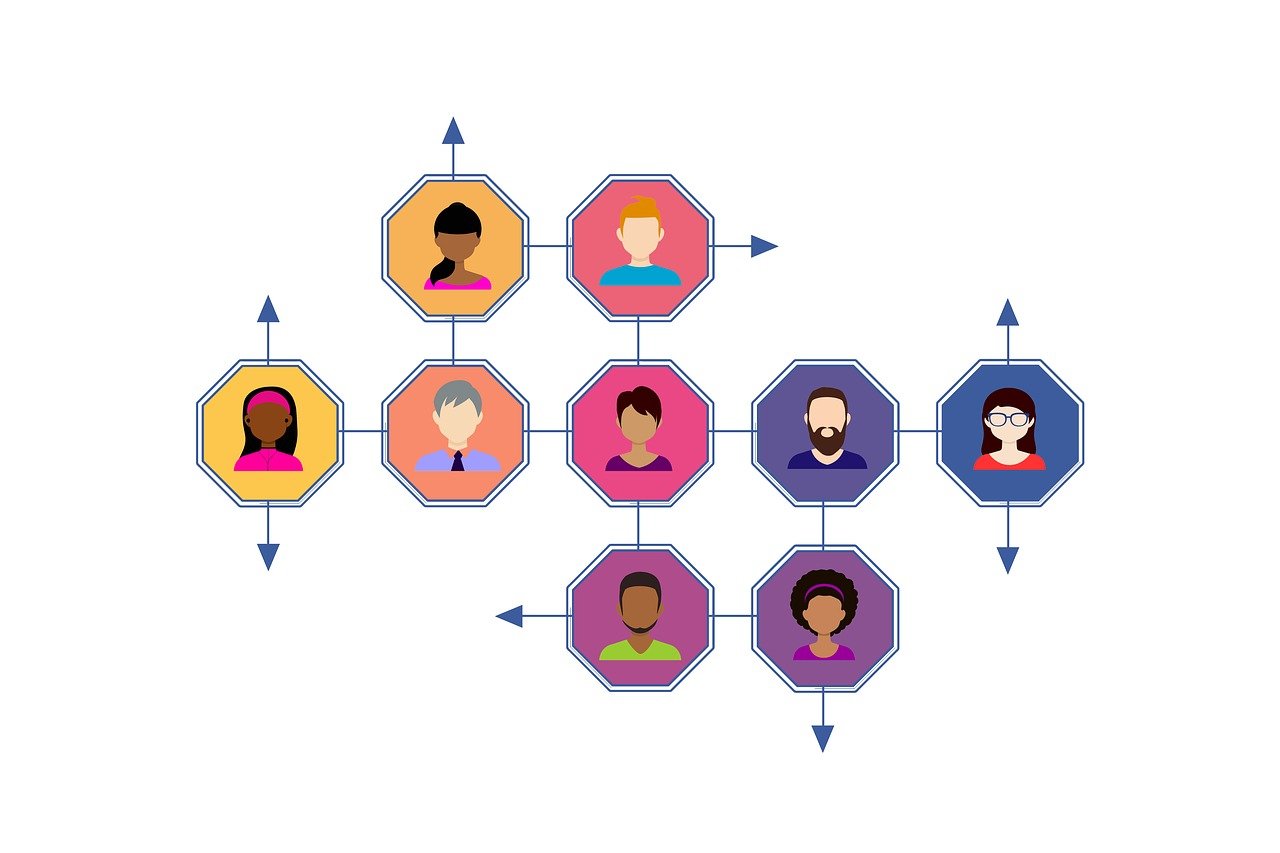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