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清末的沪杭铁路工作过,也感受了新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跃迁,华洛薇(Lola Woetzel)的家族四代人见证了中国从封闭走向全球的全过程。

华洛薇
作为全球顶级咨询机构麦肯锡的前全球董事合伙人、麦肯锡中国的创始元老之一和长期高管,华洛薇与她的先辈与中国结下深厚渊源。华洛薇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和中美交往的重要观察者,也是诸多企业和地方政府机构战略转型的亲历者与推动者。她用40年时间把“观察中国”变成一种职业,也变成一种情感。“你必须站在适当距离,才能真正看清这个国家。”她说。
当下,随着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全球政治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全球秩序正面临关键时刻,这对中美关系、全球化的未来,以及其中的每一家企业、每一个个体意味着什么?对于这种巨变的深入思考和讨论正变得越来越迫切。
近日,华洛薇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专访,回顾了她1983年重返中国、见证并参与改革的历程,也分享了她对当下全球动荡格局的判断。她认为,全球化并未终结,只是重心正在转向“南南合作”;而中国最大的优势,不是复制旧模式,而是在混乱中提出新规则。在这个分裂而复杂的时代,华洛薇依然选择相信理性、信任连接。
“我从未怀疑过中国会让世界惊艳。”华洛薇说,在这个没有赢家的地缘竞争时代,中国需要的,不只是制造能力和技术突破,更是“以系统性思维重新定义竞争”,通过结构性改革与负责任的全球姿态,为自身也为世界赢得下一个发展周期。

麦肯锡 视觉中国 资料图
四代人的中国情缘
澎湃新闻:您家族四代人与中国在近一个世纪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独特的经历让您对今天的中国有怎样的观察和思考?
华洛薇:我父亲出生在中国,我的祖父母是在1926年来到中国的。我的曾祖父母更早就在这里了,据说他们曾在沪杭铁路工作过。我的父亲在1947年随祖父母离开中国后,我在1983年回到中国。
那时,这个国家正孕育着巨大机遇,长时间的隔绝反而造就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当时很多谈论中国、对中国议题作决策的人其实从未真正踏足这片土地。
那时中国正在改革开放,营造出自由开放的环境。我当时在中山大学和复旦大学求学,可以自由接触各界人士。后来有幸加入麦肯锡,协助企业和地方政府进行合作。这段经历让我深刻理解了中国的诉求,也理解了领导层的愿景。

复旦大学 微博@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资料图
作为一个年轻人,我从零起步,这种环境让我获得了在其他地方不可能具备的竞争力。在其他国家,早有先行者建立了成熟体系;但在中国,一切都是空白。能从几乎地基阶段参与其中,我深感幸运。
我选择长时间留在中国,是因为我想参与缔造伟大。通过研究和思考,我坚信中国必将惊艳世界。我毫无疑虑地相信这一点。我知道这里具备所有必要条件,只待我们把这些“素材烹制成佳肴”。
澎湃新闻:您说过理解中国的秘诀之一是“保持一定距离”。在这里生活了这么多年之后,这句话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这是4月15日拍摄的北京日出景象。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 摄
华洛薇:我对任何事物的理解都讲究“既见树木,也见森林”。当你深陷其中时,反而难以跳脱出来真正理解它,你会过度聚焦于正在做的事。这样虽然也能学到东西,但往往要付出痛苦的直接代价。
而保持适当距离观察,不必担心个人声誉或人际关系受到牵连,反而能让我这样的人更清晰、更客观地把握局势。作为顾问,我的工作就是提供建议。寻求建议的人通常意识到:他们对自己业务或活动的投入限制了全局视野,需要像我这样的人来帮他们理清思路。无论是企业、城市还是个人,我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帮助他们理解中国、把握其内在规律,并看清这些规律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全球秩序的转折时刻
澎湃新闻:您如何定义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我们是否正经历全球秩序的重塑?
华洛薇:毫无疑问,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时代的更迭——从我们称之为“市场主义时代”的时期,转向一个全新的阶段。过去的时代,以里根和撒切尔为代表,强调市场至上,声称全球化与技术发展将自动带来更好生活。但现实是,强调市场的结果喜忧参半。
积极的一面是,人类预期寿命显著延长,中国取得了惊人的发展成果,基本消除了绝对贫困。整个东南亚、印度、马来西亚、越南乃至非洲都因此受益。这些成就虽像分散的星火,但汇聚起来的影响非常深远。
但问题是,这些进步本身改变了游戏规则。越来越多的参与者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利益诉求,每个玩家都想制定规则。我们正从“单极共识”走向“多极博弈”。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协调与化解冲突的能力。多中心权力意味着更多摩擦,而这不是哪个国家能单独避免的。
技术的逻辑也变了。过去我们讨论的是“能否数字化”,比如当年追逐互联网或传真机的浪潮。如今技术已成为无处不在的基础设施,甚至正在与人类自身融合。
问题不再是“我们是否拥有技术”,而是当技术普及后,我们如何使用它,以及如何解决它带来的不平等。因为技术能力的差异也会制造出新的社会裂缝。
我们已经拥有了力量、财富和技术,关键是如何负责任地使用它们。当被问及“应对谁负责”时,我会说,是彼此。我们要对彼此负责,不仅是本地责任,更是全球责任。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就会失去一切——财富会消失,技术会停滞,繁荣将无以为继。
我一些同事打趣说,这个问题终将解决——要么我们学会彼此负责,要么这个问题就不再需要解决了。
澎湃新闻:鉴于世界各地近期发生的事情,您认为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和自由贸易体系正在终结吗?
华洛薇:我不认为全球化结束了,有几个理由。首先,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至今并未真正参与全球化。包括在中国和美国,很多人并没有从全球化中获得好处——他们没有机会接触全球技术、缺乏全球储蓄能力和金融手段,也没有全球化的教育体系。所以对大多数人来说,全球化并未发生。

2024年12月拍摄的洋山港(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全球贸易本身是一件好事。它带来了拯救生命的技术,比如抗癌药物;它提升了人类的移动能力;它让我们可以随时与远方的亲人交流。除非人类愿意放弃这些进步,否则我们终将找到继续推动全球化的方式。而历史经验表明:人类总是能找到解决办法。
未来我预期看到的全球化,将不再只是中美之间的。中美之间的全球化已经完成,两国市场已深度整合。而未来真正的增长点,是中国与印度、中国与非洲、非洲与非洲国家之间的贸易与技术合作。那里还有大量未开发的贸易机会、技术空间和潜在需求。
过去二十多年,全球化的故事是“发达国家通过外包和市场准入构建的中美主导全球化”,我们称之为“中国冲击”。这一轮浪潮基本已完成历史使命,虽然仍将继续,但已不是未来的主旋律。
现在我们进入了“其余国家的崛起”阶段——印度、中东、非洲、拉美等国家也希望成为全球化的主角。以非洲为例,如今中东是其最大的新增外资来源国,大量绿色项目来自中东,而非中美。这种“南南合作”正成为全球化的新引擎。
中国在这一趋势中拥有重要机遇,也负有重要责任。中国应当主动开放与全球南方建立更强的贸易网络。未来全球化的新增长点就在于:中国与全球南方之间的互联互通。
中美挑战与“共输逻辑”
澎湃新闻:您认为中美是否会在经济领域出现“脱钩”?如果成真,可能引发哪些连锁反应?
华洛薇:我不想妄下定论。目前已有很多研究评估所谓“脱钩”的经济影响——无论对中国还是美国,都弊大于利。我们不应过度纠结“谁输得更多”。本质上,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博弈。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实现共赢?我始终相信,双方是有机会达成协议的。
我也相信中国企业是非常愿意投资美国的。他们乐意输出技术、人才、工程师和科学家,只需要一个公平的机会。而这些对于美国而言,同样是利好。
澎湃新闻:让我们具体谈谈绿色技术。虽然中国在新能源等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但在当前中美结构性竞争日益加剧、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不重视绿色科技的背景下,您认为中美在该领域还有合作空间吗?
华洛薇:如果只看政府对政府的合作,那恐怕所占比例非常小。要实现碳排放净零目标,仅靠政府投入远远不够,大部分资金必须来自私营部门。
每个国家都必须决定是否鼓励本国企业投资绿色技术。而推动企业投资,不只是为了“环保”——这类技术还能提升可靠性、改善空气质量、促进健康,并带来产业颠覆的机会。

这是在位于重庆市两江新区的赛力斯汽车超级工厂拍摄的智能化生产作业现场(2024年6月7日摄)。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就像电动车发展,中国其实是因为难以突破传统内燃机,才反过来率先发展电动车产业。这种“颠覆性路径”是推动投资的好理由。
我相信美国也可以选择这条路。归根结底,地球不关心我们的政治立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迟早要推动和部署解决方案。
澎湃新闻:在当前政策环境变化下,中国企业在美洲、东南亚等地的投资也面临越来越多不确定性。这种情况下,企业如何做出明智的投资决策?
华洛薇:最重要的一点是:亲自去当地。很多人误解中国企业怕风险,恰恰相反,他们天生在风险中生存。只要实地了解市场,合理规划投资路径,就能大大降低风险。
比如投资时,可以先小规模试水,如先建一个小工厂验证市场,再逐步扩张,而不是一开始就投入巨额资本。这种渐进式战略正是中国企业的优势所在。
澎湃新闻:您对中国一些严重依赖出口的城市和企业,有什么建议?
华洛薇:必须灵活调整市场结构。如果一个市场收缩了,就要开拓其他市场,同时利用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系统性优势。
城市可以尝试利用人民币国际化契机,通过人民币计价的项目融资连接“一带一路”投资,建立跨境资金循环通道。同时,发展数字化生态、金融体系,像杭州一样为本地企业打造“一站式全球化服务平台”。
澎湃新闻:您曾说“战略是一个发现过程”,那么在全球格局动荡、秩序重构之际,中国如何找到自己的战略路径?
华洛薇:说实话,我们现在仍然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才刚刚开始。
虽然现在《财富》500强中,中国企业数量超过美国,但它们的海外营收平均仅为20%,而美国企业是40%。这说明中国企业仍高度依赖本土市场,全球运营经验相对不足。
如果中国希望成为真正的全球经济体,那就必须提升国际化水平。这意味着要培养更具全球视野的人才,要能在塞尔维亚工作得像在温州一样得心应手。
此外,中国企业还要加强“开放式协作”的能力。目前的短板在于沟通习惯——很多企业“只会说中文”,即使有翻译,交流效率仍受限。这不仅是语言问题,更是心态、管理方式和人才结构的问题。
给未来3-5年的建议
澎湃新闻:您认为中国接下来最紧迫的产业改革任务是什么?
华洛薇:很多行业已是“红海”,产能过剩问题严重,根源在于信贷系统无法有效分配风险——大量资金流向回报率低的项目。中国企业在全球的资本回报率明显低于国际同行,这说明我们金融市场尚不成熟。
必须推动金融体系改革:完善债券市场、提升透明度、强化信用评估机制和破产重组效率。尤其要把资本从房地产引导至科技创新。这是一场结构性转型,不能再靠“砸钱”解决问题。
澎湃新闻:作为战略顾问,您对未来3到5年中国政府和企业有何建议?
华洛薇:第一,对各地方政府来说,要聚焦本地议程,想清楚“全球化”意味着什么。它不只是出口,而是构建本地企业全球竞争力的生态,包括贸易协定、城市间合作、数字和金融生态系统建设等。
第二,中国企业要认识到:没有退路,必须走出去。必须继续在全球语境下发展技术,打造全球供应链与分销网络,真正进入海外市场。
第三,企业要学会成为“伙伴型”组织。未来的成功企业,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连接性的。
至于中央政府层面,我暂时没有太多建议。当前我们仍在观察中国如何持续与外界互动。但我始终坚信,过去40年全球化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红利,我们绝不能背弃它,必须找到继续前行的路径。
澎湃新闻:您去年从麦肯锡卸任,而您的职业生涯黄金期几乎全部留在中国。在这个日益分裂的世界里,尤其面对中美紧张局势,您会给中美年轻一代什么建议?他们该如何保持希望?
华洛薇:我虽然离开了原来的公司,但现在创办了自己的城市发展咨询机构,依然活跃。我想鼓励年轻人保持这样的心态:人生没有Plan B(备选方案),只有必须坚守的主线。你必须投身自己热爱的事业,必须坚持那些你内心认同的、对个人成长有意义的事,否则只是虚度光阴,而世界从不会停下脚步。
我还想说,不要美化过去。回顾历史,我们总是只记住光鲜的一面。可身处当下时,是复杂和混乱的。但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要珍惜当下的机遇。今天我们有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繁荣和技术红利。而年轻人,正处在人生最适合投资未来的阶段。他们没有“过去”,只有“现在”。他们应当活在当下、善用当下。
我今年60岁,仍然觉得自己还有20到30年的路要走。哪怕生命最后一天,我也会继续“为未来投资”——哪怕那已不是我的未来,而是下一代的未来。
丘吉尔曾说过:“我是个乐观主义者,因为做别的貌似没什么用”。“你想做什么呢?难道要一直愁眉苦脸吗?不如保持乐观吧。”
(实习生孙旺琪对本文亦有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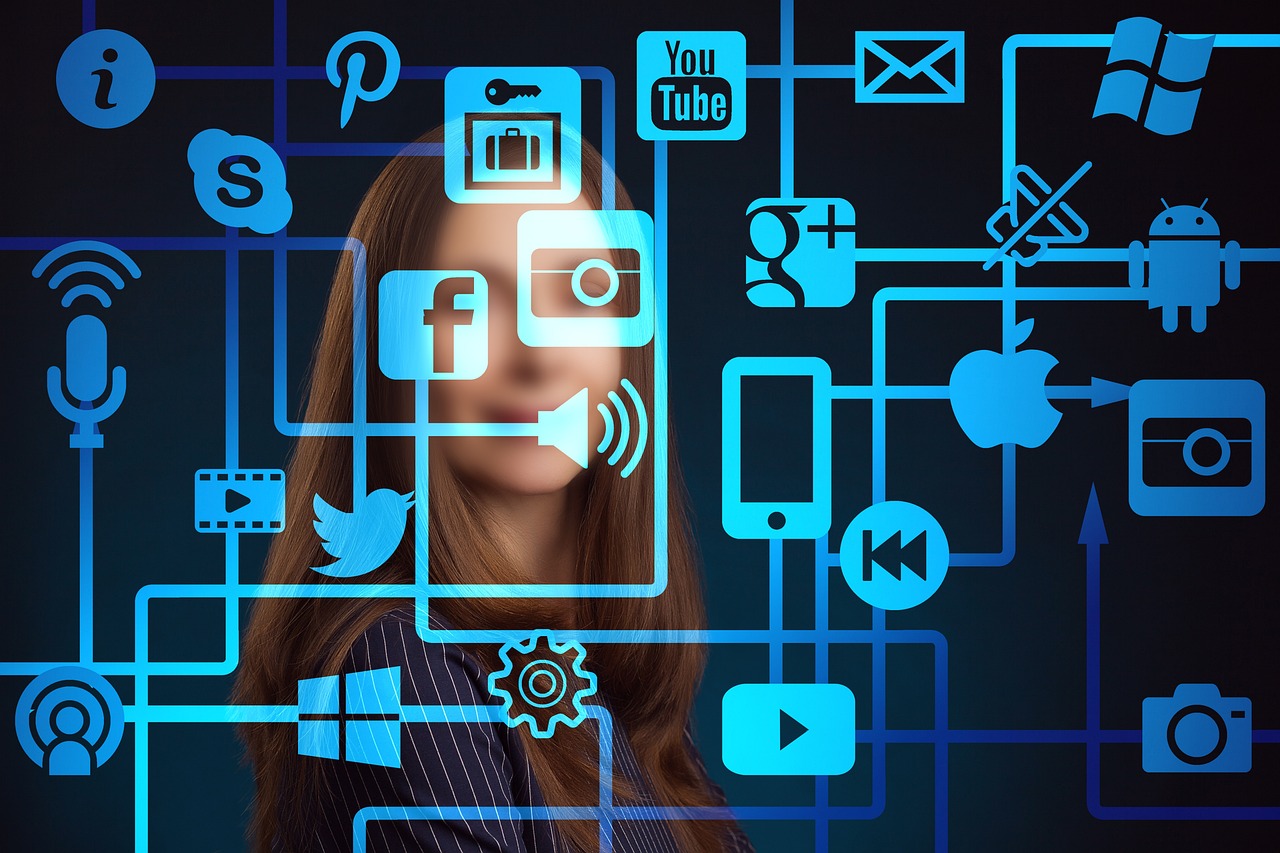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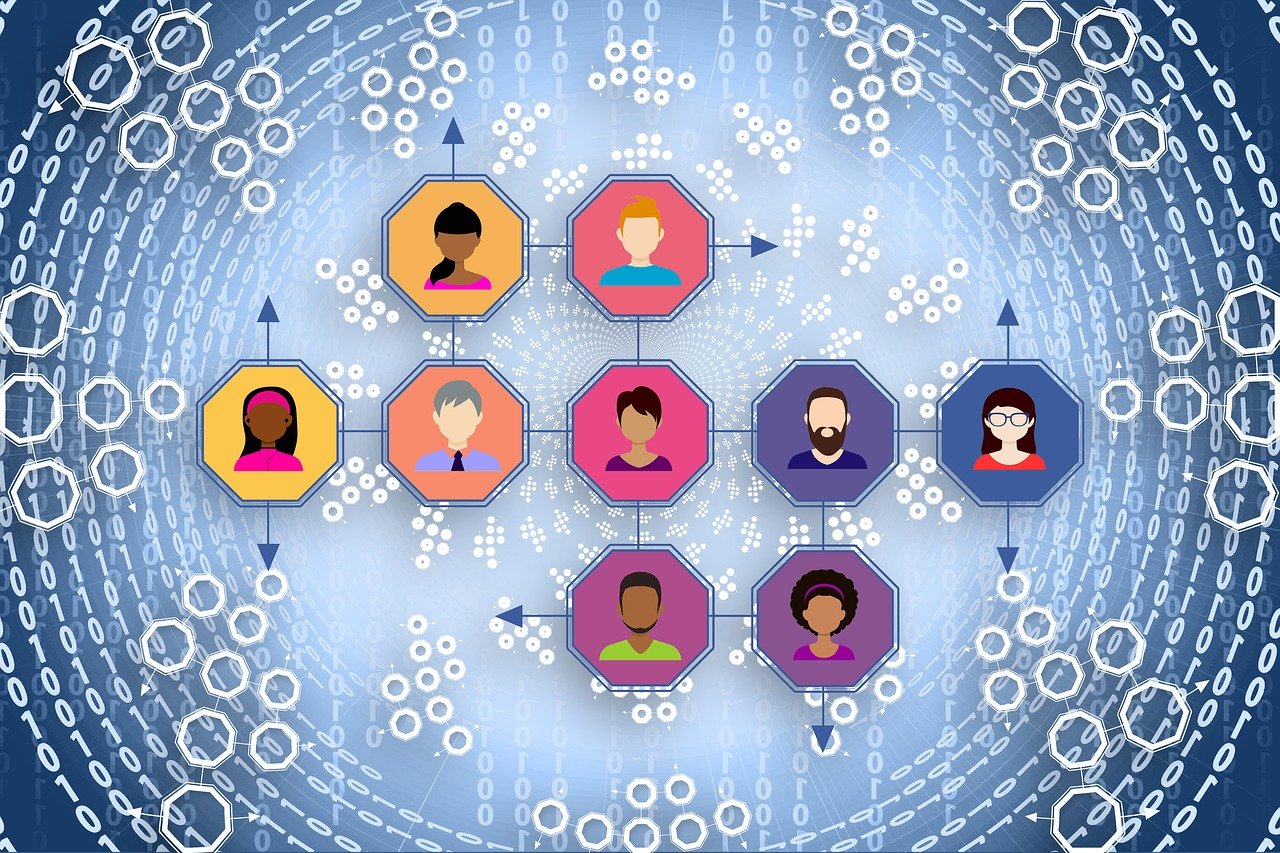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