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来到墨西哥的人,大多对不同种族的着装印象深刻。英国多明我会修士托马斯·盖奇(Thomas Gage,约1603—1656)在17世纪中期访问墨西哥城时,发现大多数衣服都是用彩色丝绸制作的。他记录道:
男人和女人的服装都很夸张,使用的丝绸比其他织物要多……绅士的帽子上经常会饰有钻石做的帽带和玫瑰,商人的帽子上则多是用珍珠做的帽带……黑摩尔人或黄褐色的年轻奴仆的工作非常艰辛,但她的项链和珍珠手镯,以及她耳坠上的硕大珠宝,彰显时尚……黑摩尔人和黑白混血儿的装束……极为轻盈,她们的车乘也让人心动。许多社会地位较高的西班牙人都沉迷于她们的美色,甚至为她们抛妻弃子。
尽管有些言过其实,但这一记录仍可说明丝绸在当时是最受欢迎的布料,在西班牙社会中被广泛使用。不论是在男装还是在女装中,丝绸时装都很流行,而且很多时候都饰有贵金属和珠宝。这种奢侈品,涵盖了各类日常装饰,包括马车的装饰。就像在中国一样,较低阶层也能穿上、用上丝绸。盖奇在文中划分了两类人:“黑摩尔”(blackamoor),即皮肤较黑的摩尔人(这个词最初是指穆斯林,后来通常指非基督徒);“穆拉托”(mulattoes),指的是黑人与白人的混血儿。在西班牙人眼中,这些人本来是下等人,而且不同等级体系之间的通婚通常是不合规的。但由于这些人的衣着和马车都很考究,所以西班牙人喜欢在他们当中寻找情人。
在整个行程中,盖奇对墨西哥城的景象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和中国一样,这座城市成为时尚的中心并一直保持着这个地位。西班牙人阿特米奥·德·瓦勒-阿里斯佩(Artemio de ValleArizpe,1884—1961)记录道,在18世纪的墨西哥城,“普通人穿着丝绸裙子或印花布,上面装饰着金银条带;色彩鲜艳的腰带上,还有金色的流苏,从前面和后面翻下来,装点裙边”。除了精美的织物,贵金属也广泛用于服饰设计。
欧洲和亚洲的纺织品,在近代美洲都可以买到,并且深受偏爱。盖奇还发现,当时的人们穿着“产自荷兰或由上等中国亚麻布制成的套袖,上面绣有彩色的绸缎”。太平洋和大西洋两条贸易路线都连接了墨西哥,所以美洲人认为来自西班牙和瓦哈卡的丝绸都是劣质的。从当时人们的遗嘱中,也可看出中国丝绸在家庭中的普遍性。伊莎贝尔·巴雷托·德·卡斯特罗(Isabel Barreto de Castro,1567—1612)的丈夫是一名西班牙水手,他在最后一次从秘鲁到太平洋的远征中去世。根据他的遗嘱,巴雷托继承了许多来自中国的贵重物品,包括织物和珠宝,还有在阿卡普尔科的满屋的丝绒,价值七千比索,以及四个精美的箱子,满载织物和中国服饰。能看出来这是一个富裕家庭,他们利用各种外国关系,往自家的衣柜塞满了进口织物。
追求异国情调
遍览整个西班牙帝国,穿戴中国丝绸的现象都十分常见。由于马尼拉在地理位置上与中国相邻,所以这种情况也在马尼拉普遍存在。历史学家阿尔赞斯·德·奥尔赛·维拉(Arzáns de Orsúa y Vela,1676—1736)记载,马尼拉的流行商品包括“来自印度的谷物、水晶、象牙和宝石,来自斯里兰卡的钻石,来自阿拉伯的香水,来自波斯、开罗和土耳其的挂毯,来自马来半岛和果阿的各种香料,以及来自中国的白瓷和丝绸服饰”。中国丝绸和其他精美商品的贸易“绝对是马尼拉存在的理由(raison d’etre)……在马尼拉,中国人带来了几乎所有可以运往新世界的货物,并且几乎完成了所有的商务和工艺”。这种时尚一旦传到美洲,就会影响墨西哥和秘鲁。秘鲁总督孔德·蒙特雷(Conde de Monterrey,1560—1606)观察到,“赤贫的人、黑人和穆拉托男女、桑巴伊戈(sambahigos,印第安男人和非洲女人的儿子)、许多印第安人和混血儿都可穿戴丝绸,而且数量很多”。这些记录还着重介绍了黑人、印第安人和混血儿后代穿戴丝绸的情况。这些记录者没有提到西班牙人的时尚,说明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丝绸这种织物,而且中国丝绸的风格也确实在16世纪之前就在大都市中流行起来了。由于墨西哥商人在15世纪60年代末就已经开展了很多独具前瞻性的商业活动,所以在人们刚刚发现菲律宾时,墨西哥城早已成为他们世界的中心。
穿戴亚洲和欧洲丝绸的时尚,代表了个人的奢侈生活方式。这也是人们越来越追求身份认同的一大原因。正如历史学家马修·托马斯(Matthew Thomas)所言,西班牙人、克里奥尔人(Creole)、非洲人或美洲各地原住民男女穿戴中国丝绸,以及中国商人和农民使用西班牙银元,这些事情使他们直接参与了近代世界经济的大扩张。艺术史学家丹尼斯·卡尔(Dennis Carr)指出,来自亚洲和其他外国的装饰品,使美洲人民能够超越他们殖民地公民的地位,直接展示自己的贸易能力与商业信誉。他们对时尚的展示,既是出于对奢侈品的欣赏,也是出于对参与外国商品流通的热切渴望。
正如盖奇所观察到的,欧洲和亚洲织物的大量消费,不仅是因为这些织物精致细腻,还因为它们来自国外。正如下文将讨论的那样,亚洲工匠引入的风格大受欢迎,很可能是因为这些织物风格的独特性,以及它们对遥远文明的象征。亚洲花卉纹样的流行,可能也有同样原因,下文将分析这一过程。在这种消费环境和对全球热潮的追随中,墨西哥人感知到了他们优越的历史与地理意义。他们热衷于改变,并且逐渐建构起自己在西班牙帝国和太平洋航线上的独立商人地位。
因此,购买亚洲丝绸也象征着人们从西班牙统治之下获得独立的集体愿望。丝绸贸易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资本,使商业行会的大商人成为墨西哥的核心力量。原本商人们只能销售大西洋舰队运载的货物,而现在太平洋贸易给他们提供了一条高利润的投资渠道。他们的特权地位,使他们能够支撑国防,并捐出大量的钱款给皇家财政。商业贸易产生的利润,使他们对帝国足够忠诚,并在各类国家决策和与世界大都市的交流中获得话语权。
大帆船运载的货物,主要是生丝与未染色的白色织物。来自中国的白色织物备受欢迎,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大多数亚洲织物都用草本染料,可能对水或阳光非常敏感,极易掉色。大多人都认为,胭脂红色比红花染出的颜色持久得多。另一方面,白色的生丝也使当地工匠能够自由地迎合当地人的喜好。当地手工艺人有时会重新编织已经染色的织物,创作出本土图案与欧式图案。这种亚洲生丝、美洲染料与欧洲设计的结合,是墨西哥近代时尚的特色。由于文化的多元性,各地的时尚并非趋同,而是结合了不同的传统与创新风格。有时呈现异国情调,有时则呈现传统的本土风格。
虽然明朝生丝原料的主导地位毋庸置疑,但由于文化与时尚的差异,明朝丝织品的地位却没那么高。消费者一般都偏好符合其文化背景的设计,而且当地教会也需要购买具有宗教 意义的织物。然而,亚洲设计的引入,使美洲殖民地的审美更为多元。来自亚洲的加工纺织品,促进了美洲社会产生丰富多样的物质文化。它不仅影响了西班牙人和殖民官员的圈子,而且也影响了原住民社区。贝弗利·勒米尔总结道:“在这个不断扩大的市场中,殖民地的美洲原住民以改良刺绣花色的纪念品、家居用品和时装来争取地位,因为他们积极响应了物质文化的全球化趋势。”这种“文化融合”是殖民地生活中永恒的核心。因此,在市场上随处可见中国丝绸、印度棉布、欧洲亚麻布和羊毛以及当地布料的融合。
文化的多元性跨越了空间和时间,构建了更加全球化的设计体系。以中国明朝织物为例,双头鹰暗示了哈布斯堡的王冠,而心形的花瓶则暗示了与菲律宾奥斯定会(Augustinians)的联系。虽然已有现成的传统设计套路,但是很多丝绸织工还是会自行设计纹样。这块丝绸上的鹰和花瓶周围的交错纹样,就是仿照中国青花瓷上最常见的纹样。诸如莲纹、菊纹等中国风格的花卉图案,还是会出现在19世纪马尼拉生产的披肩上。这件织物融合了不同文化背景的设计思路,可谓与时俱进。虽然这些纹样主要与西班牙王室有关,但也是不同文化相互交融的范例。除此之外,复杂的设计也意味着需要投入更多劳动力与制定更高的定价。
亚洲的花卉纹样是早期全球化最明显的象征之一。花卉有着不同的功能和情感意义,象征着不同的植物、生命周期,以及女性气质。因此,花卉设计不仅代表着异国情调,还反映了对偏远地区的认知。中国和美洲的匠人,还有构建中国、美洲大陆纽带的商人、水手与海运专员,都在亚洲花卉纹样的传播中贡献了力量。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消费者偏爱并支持这种交流和设计的融合。在这融合的过程中,有无数人参与其中,这也说明了审美全球化的深远影响。
挪用中国和亚洲花卉纹样的时尚,绝不仅限于纺织品生产和服装设计。这样的挪用,还可反映出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园林文化的极大兴趣。由此,越来越多有关中国植物和花卉的绘画和书籍得以面世。正如艺术史学家王廉明指出的那样,欧洲主顾最喜爱中国园林植物,而非药材和其他异国植物。这种偏好,说明欧洲人相信中国优越的农业条件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并促进欧洲学术团体的壮大。这种观念,也说明了他们为什么要采用中国的蚕业知识。
从亚洲到美洲的移民也带来了新的风格。许多亚洲移民拥有专门的纺织店。可以从“中国姑娘”(china poblana)的故事中看出他们的影响。据说,这位“中国姑娘”与当地的墨西哥人一起设计、推广了新款的丝绸服饰。这种服饰主要是一种无袖的、镶有金边的黑色丝织品,还饰有红色、白色和绿色的刺绣。许多中国人和美洲原住民都穿这种服装,其后来慢慢演变成墨西哥民族身份的一大标志。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女孩”指的是莫卧儿帝国的“公主”米拉(Mirrha/Meera),因为当时她推崇莫卧儿印度风格的服装,此举带来了很强的影响。另一种合理的推测是,“中国姑娘”原本生活在菲律宾,后来在被海盗俘虏后随着一艘大帆船来到了墨西哥。无论她的身份如何,这段故事证实,亚洲移民和亚洲工匠在墨西哥历史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时尚灵感。

“中国女孩”立像,资料来源:卡拉· 安德鲁(Karla Andrew)拍摄于普埃布拉的一处商业广场,2013年。
据记载,随着马尼拉大帆船的启动,出现了第一波跨太平洋的亚洲移民潮。来自契丹(Cathay)、西邦戈(Cipango,日本)、菲律宾、东南亚各王国和印度的旅行者在墨西哥被统称为“中国人”(Chinos)或“中国印第安人”(Indios Chinos)。历史学家爱德华·斯莱克(Edward Slack)讨论过这些移民群体,他估算,在两个半世纪的跨太平洋接触中,至少有四万移民踏上了墨西哥的土地。这些中国人多是去当水手、奴隶和仆人,一般都是在阿卡普尔科上岸。当时的大多数海员,都是菲律宾人、常来人或来自马尼拉附近军港的华裔。后来的第二波移民主要是从海上运送的仆人和奴隶,他们为西班牙地主工作。
相当多的移民留在了墨西哥城,服务当地商人。早在17世纪20年代,托马斯·盖奇就记录道:“金匠的商店和作品最值得钦佩。印第安人和中国人已经成为基督徒,每年都会到这里来,他们在这一行业中已经超过了西班牙人。”在马约尔广场(Plaza Mayor),以西班牙露天市场的摊位和小商店为主的商业中心,是以马尼拉的华人区—巴里安市场命名的。如果中国人零售商品,他们就需要向西班牙国王缴纳皇家贡品,这说明中国商人群体16世纪末就已经融入了西班牙的财政体系。随着来自亚洲的移民数量不断增加,很多领域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例如,1635年,有西班牙理发师向市议会投诉,在马约尔广场有多达200名华人开办了理发剃须店。收到投诉后,官员们决定将华人理发店的数量限制在12家以内,而且所有的华人店铺都必须开在郊区。
随着丝织品等织物的全球流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回收和仿制。在那几百年里,二手服装贸易蓬勃发展,占据了消费市场的一大部分。二手服装的回收利用,也促进了纺织技术的改进和国内商贸体系的完善。与中国同行一样,太平洋彼岸的工匠也喜欢融合两种不同文化的设计。在1644年清朝入关后,明朝官服上的补子被运到了美洲。这些补子描绘了形形色色的禽鸟走兽,象征着文武百官的官阶。这些补子可以是通货,可以是衣柜中的收藏,也可以是重复使用的重要材料,可以说是从各个维度上提升了服装的价值。具体而言,它们衍生出墨西哥丝织品中的新设计,比方说一张17世纪的挂毯就出现了鹈鹕纹样(图 3.2)。鹈鹕本是传统的基督教象征,在此被渲染成中国神话中凤凰的样子,嘴很短,尾巴很长。鹈鹕的姿态、翅膀的刻画风格,以及嘴里叼着花的细节,都很像明末的仙鹤补子(图 3.3)。通过将亚洲元素与传统的欧洲文化符号相结合,墨西哥工匠融汇了本土风格与外来风格,这件织物既是本土的,又是外来的。回收和仿制,为商业流通和市场联系增添了活力,提供了更多样的文化元素。

饰有鹈鹕纹样的墨西哥挂毯。资料来源:现藏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纺织博物馆,馆藏号91.504,由乔治·赫威特·迈尔斯(George Herwitt Myers)于1951年收入馆中。

明末的仙鹤补子。资料来源:现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大多数经过加工的织物,都是由女性再加工的。女工们经常接到订单,为那些需要廉价服装的市民修补、售卖一手与二手物品。这样的情况,多半加强了当时人们的消费能力。女性在衣着贸易中的产业,扩大了消费市场的范围与规模,同时也保障了她们自己及其家庭的生活。比方说明代中国的女性,就大大带动了时尚潮流。在美洲其他地区,也有很多女工参与这类贸易。例如,勒米尔讨论过克里奥尔女性挪用亚洲棉被的设计风格,在墨西哥的殖民前哨生产独创版本的情况。这一行业为不同年纪的女性提供了饭碗,实际上与在中国南方普遍出现的情况类似。正因如此,妇女赢得了更高的经济地位。
西班牙红
与中国文化环境一样,红色也是西班牙王室的首选。最初,只有王室和教会可以使用红色。在欧洲各地,红色也都很抢手。1535年,德国农民甚至发动了一场起义,要求获准穿着红色服装。这种对红色的追求也传到了美洲,并恰好呼应了当地传统。新大陆上的西班牙人注意到,原住民的衣服上也有浓烈的红色。这种颜色,取自一种叫做胭脂虫的小昆虫制成的天然染料。
胭脂虫主要生长于墨西哥胭脂仙人掌的关节和叶子上。虽然胭脂虫的身体呈白色,但它被挤压后就会爆出鲜红色的汁液。虽然在拉丁美洲的许多地方都能找到胭脂虫,但生长于墨西哥的胭脂虫比其他地方的大出一倍之多,而且可以产生更深、更鲜艳的红色,无疑是最优选择。在西班牙殖民之前的中美洲,红色染料是用来表现原住民世界观和宗教信仰的重要元素。
新世界其实也推进了旧世界的时尚潮流。胭脂虫的利用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当时,无论是政论家、自然学家、商人、国王、总督还是传教士,都对胭脂虫有着浓厚的兴趣。从16 世纪初开始,来自欧洲的传教士就开始组织原住民在仙人掌上培养胭脂虫,这样可以提高收益,并将原住民社区纳入政府控制范围。很快,这种染料就引起了西班牙王室的注意。当西班牙国王在1523年听说胭脂虫时,他便向瓦哈卡高地的侯爵埃尔南·柯尔特斯下令,要求侯爵立即报告是否已经在墨西哥发现了胭脂虫。国王认为,如果真的已经发现了,那么就要算清是否有足量的胭脂虫可供出口,并“尽一切可能努力收集”。胭脂红是风靡欧洲的红色染料,所以国王的这一命令说明,寻找有价值的原材料是西班牙王室殖民墨西哥的主要目标之一。
红色的渴望和随之而来的利润,加快了胭脂虫从阿兹特克人那里转移到西班牙朝贡体系的进程。1536年,国王从瓜哈巴(Guaxuapa)收取了28车的格拉纳(grana,加泰罗尼亚语“红色”)贡品。1554年,西班牙商人弗朗西斯科·塞万提斯·德·萨拉萨尔(Francisco Cervantes de Salazar,约1514—1575)宣称,墨西哥盛产格拉纳,并大量出口到西班牙。

生长于美洲、可结种子的胭脂仙人掌。资料来源:迭戈·德·托雷斯·瓦加斯(Diego de Torres y Vargas):《关于新西班牙和秘 鲁各天主教教区的历史、组织和地位的报告》(“Reports on the history, organization, and status of various Catholic dioceses of New Spain and Peru 1620—1649”),现藏于纽伯里图书 馆(Newberry Library),馆藏编码 Vault Ayer MS 1106 D8 Box 1 Folder 15。
在17世纪,胭脂虫的培育范围更加广泛,因此相关记载十分常见。上图出自《关于新西班牙和秘鲁各天主教教区的历史、组织和地位的报告》,可以追溯到1620年至1649年之间,是一份最能反映墨西哥教会史的抄本。此抄本收录了一大部分关于墨西哥米却肯教区的报告,因此图中描绘的很可能也是米却肯地区的胭脂虫采集。对西班牙王室而言,这是从社区收取贡品的重要来源之一。插图中的仙人掌巨大,可以容纳很多胭脂虫。在绿色仙人掌的衬托下,胭脂虫体呈白色,大量聚集在一起。插图下方,两个原住民从一面巨大的仙人掌叶片上摘取胭脂虫,并将其挂到碗里收集起来。他们的衣服都饰有深红色条纹,大概都是用胭脂虫染成的。此外,不论男女,都会采集胭脂虫,说明胭脂虫的采集也是一种社区产业,就像种桑养蚕一样。在《报告》中收录这样的图像,说明人们(尤其是教会的人)对胭脂虫 的培育和采集有着强烈的兴趣,认为这是西班牙朝贡和贸易体系中的重中之重。
生产胭脂红并不需要特别肥沃的农田,只要一小片仙人掌林就足够了。因此,胭脂虫为西班牙殖民者提供了解决原住民社区土地短缺的方案。以米亚瓦特兰(Miahuatlán)省的奥塞洛特佩克(Ocelotepeque)镇为例,由于当地土地贫瘠,无法种植玉米,所以当地人绞尽脑汁地改善土地的质量。唯一的好办法,就是改养胭脂虫。另外,胭脂虫也很容易受到气候和恶劣天气的影响。意外的霜冻、大雨或干旱,都会导致颗粒无收。所以胭脂虫对天气的敏感性也解释了为什么瓦哈卡地区会成为胭脂虫养殖的中心:当地土地贫瘠,不适合开展其他农业,但是气候却相对稳定。此外,瓦哈卡地区的农业社区较为密集,适合培育胭脂虫和生产染料。只要改养胭脂虫,那么此地与城市市场的联系就会进一步加强。这不仅是因为西班牙人需要很多染料,还因为原住民越来越集中于养蚕、养胭脂虫,所以社区需要从外部采购大量日常用品。
采集和培育胭脂虫并非易事。贡萨洛·戈麦斯·德·塞万提斯(Gonzalo Gómez de Cervantes,1537—1599)在《与胭脂虫有关的内容一览》(“Relación de lo que toca a la grana Cochinilla”)中详细描写了胭脂虫的培育,描述了胭脂仙人掌从播种、养护到发芽的过程。照看胭脂虫需要有极大耐心。人工培育可大大提高野生胭脂虫的质量。据洪堡说,养殖的胭脂虫与野生胭脂虫相比,不仅体积更大,还有着更厚的棉质表皮,可以产出高质量的染料。
养殖胭脂虫和养蚕一样,都需要在它们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密切照料。在此过程中,可能会有各种害虫和鸟兽前来骚扰。由于胭脂仙人掌通常不足1.2米高,蜥蜴、老鼠以及禽鸟会很容易吃掉胭脂虫。人们还需要剪掉花朵和果实,以便防止飞虫在那里产卵。此外,由于南风对胭脂虫有害,还必须为植物遮挡南风。有时,人们需要用灯芯草制成的垫子盖住仙人掌,以保护幼小的胭脂虫免受寒冷天气的影响。后来,人们为养殖胭脂虫采用了大规模的保护措施。正如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罗宾· A.唐金(Robin A. Donkin)记载:
自18世纪以来,已经出现了超过五万个大规模的种植园。每一个这样的种植园有时可以占据大约25平方米的区域。周围装有泥墙或栅栏,用来防风、防尘,有助于驱赶可能吞吃胭脂虫的禽鸟。霜冻和雨水也可能造成胭脂虫的大量损失。因此,当人们预报霜冻时,就会点燃火把;有时也会用木头和稻草搭起雨棚,防止仙人掌被大雨冲刷。
像这样的保护措施,需要提前很久开始准备。
为了适应当地的气候,某些地区采取了一种叫做“胭脂虫迁徙”的策略,这需要很大的工程量。平原地区通常在5月至10月下雨,山区则在12月至次年4月下雨。每到下雨时,原住民一般不覆盖果实,而是将盖着叶子的雌胭脂虫分层放在篮子里。随后,他们将这些篮子带进山区,让雌胭脂虫在旅途中繁育。“迁徙”可以使胭脂虫保持干燥,是行之有效的策略。
将胭脂虫制成红色染料,又需要经历另一个复杂的过程。每公顷的仙人掌,可以收获大约250公斤的胭脂虫。首先需要用热水烧死胭脂虫,并将其放在太阳底下烘干。有时甚至需要放在铁锅里烘烤,做成砖红色的染料,以备装运。由于七万来只胭脂虫只能生产出一磅染料,所以这个过程需要投入巨大的劳动成本,这样制作出来的染料也就十分昂贵。
胭脂虫在西班牙帝国的贸易扩张中独具意义。据胭脂虫专家雷蒙德·李(Raymond Lee)称,胭脂虫的重要性,在16世纪下半叶尤为显著。与养蚕业一样,胭脂虫也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成为行政体系中的重要部分。总督恩里克兹鼓励原住民养殖胭脂虫,要求他们种植仙人掌,照料成熟的胭脂虫,并在其中的各个阶段“勤奋工作”。17世纪,西班牙政府的支持和信贷供应,从各个方面促进了胭脂红的生产。在收成最好的时候,胭脂红甚至可能产生超过200万比索的利润。到了18世纪,胭脂红产业已经成为瓦哈卡地区的一个经济支柱。在墨西哥的大部分地区,胭脂虫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培育的,但是瓦哈卡地区主要是以种植园培育的。洪堡曾观察到,在奥科特兰(Ocotlán)附近,有些庄园里有五六万只成排养殖的胭脂虫。
为了促进胭脂红的生产,西班牙政府同时承担了资本家和出口商的角色。墨西哥城的商人和西班牙的商人,都会向农民预付定金,以确保胭脂虫的生产。此外,新型的胭脂红生产与贸易系统在17世纪形成。这个系统中有原住民家庭担任生产者,由市长、副市长与代理人等殖民地雇主担任监督。瓦哈卡州的商人需要在胭脂虫收获季之前支付定金,并与这些殖民地官员合作。囤积足够胭脂红的商人,之后会将染料运到委拉克鲁斯港,交予当地企业家或出口商。一旦运抵欧洲,加的斯(Cadiz)或塞维利亚的商人就会把胭脂红再次出口到欧洲更大的纺织中心。这样一来,墨西哥和西班牙的商人就可获得最大的利益。
由于贸易产生了无比丰厚的利润,所以诈骗就成了常事。为了应对胭脂红贸易中的各种问题,政府已经立法来控制胭脂虫的加工、分级和出口。这需要政府专员组成监察网络,严格执行法律法规。由此,贸易诈骗行为得到了遏制,染色过程也更为规范。1550年,第一部关于检视胭脂红质量和销售渠道的条例出台,防止了商人虚报重量,欺诈客户。这部条例还提到,需要对违法三次以上的人进行加倍惩罚。到了1592年和1594年,政府又颁布了一系列法律,阻断了以胭脂红诈骗的路径。不过,这也说明了当时诈骗行为的普遍性。
胭脂虫被引入欧洲后,很快就取代了以前用于制作红色染料的绛蚧(kermes)。从墨西哥胭脂虫体内中提炼出的明亮的大红、深红和紫红,淘汰了所有的竞品,广受追捧。第一批墨西哥胭脂虫于1526年抵达西班牙,1552年抵达安特卫普,最后于1569年抵达英国。据1555年2月上呈的一份报告,普埃布拉、特拉斯卡拉(Tlaxcala)、乔鲁拉(Cholula)、特佩亚卡(Tepeaca)和邻近城镇每年生产的胭脂红,估算价值共为20万比索。其中产出的大部分胭脂红都流向了欧洲。总督恩里克兹在1574年报告说,当年生产的胭脂红可以说是史上最多;1575年,胭脂红约有七千阿罗瓦(arrobas,旧时西班牙的重量单位)的出口量。次年,出口量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万两千阿罗瓦。冈萨罗·戈麦斯·德·塞万提斯(Gonzalo Gómez de Cervantes)在1599年估算,墨西哥的平均胭脂虫出口量为一万至一万两千阿罗瓦。上述史实正好说明,塞万提斯的说法是正确的。继白银之后,胭脂红成了人们眼中从美洲殖民地出口的又一核心产品。在16世纪和17世纪,胭脂红加强了美洲对构建欧洲丝绸时尚的贡献。
这种昂贵却易于运输的染料,使西班牙人大获其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胭脂虫的价格都与黄金相当。对西班牙政府而言,与胭脂虫相关的信息始终都是最高机密。1688年的《哲学学报》(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第一次尝试破译胭脂虫的秘密,即认为胭脂虫是一种由仙人掌果(prickly pear)孕育的昆虫。直到1704年,才有一篇专文提出胭脂虫是一种有六条腿的昆虫。西班牙人限制了有关胭脂虫繁育方法的信息传播,私自出口胭脂虫就是死罪。西班牙保护胭脂虫,无非是为了垄断鲜艳染料的生产,使那种红色更加神秘,更受追捧。在知道西班牙的胭脂虫是什么之前,欧洲人曾把胭脂虫称为“西班牙绛蚧”(Spanish kermes)或“西班牙粉末”(Spanish powder)。就像丝织品一样特定地区可以用来命名广受欢迎的颜色。在全球时尚的语境中,地方性一直都是重要议题。

(本文选摘自《尤物:太平洋的丝绸全球史》,段晓琳著,柴梦原译,光启书局2024年7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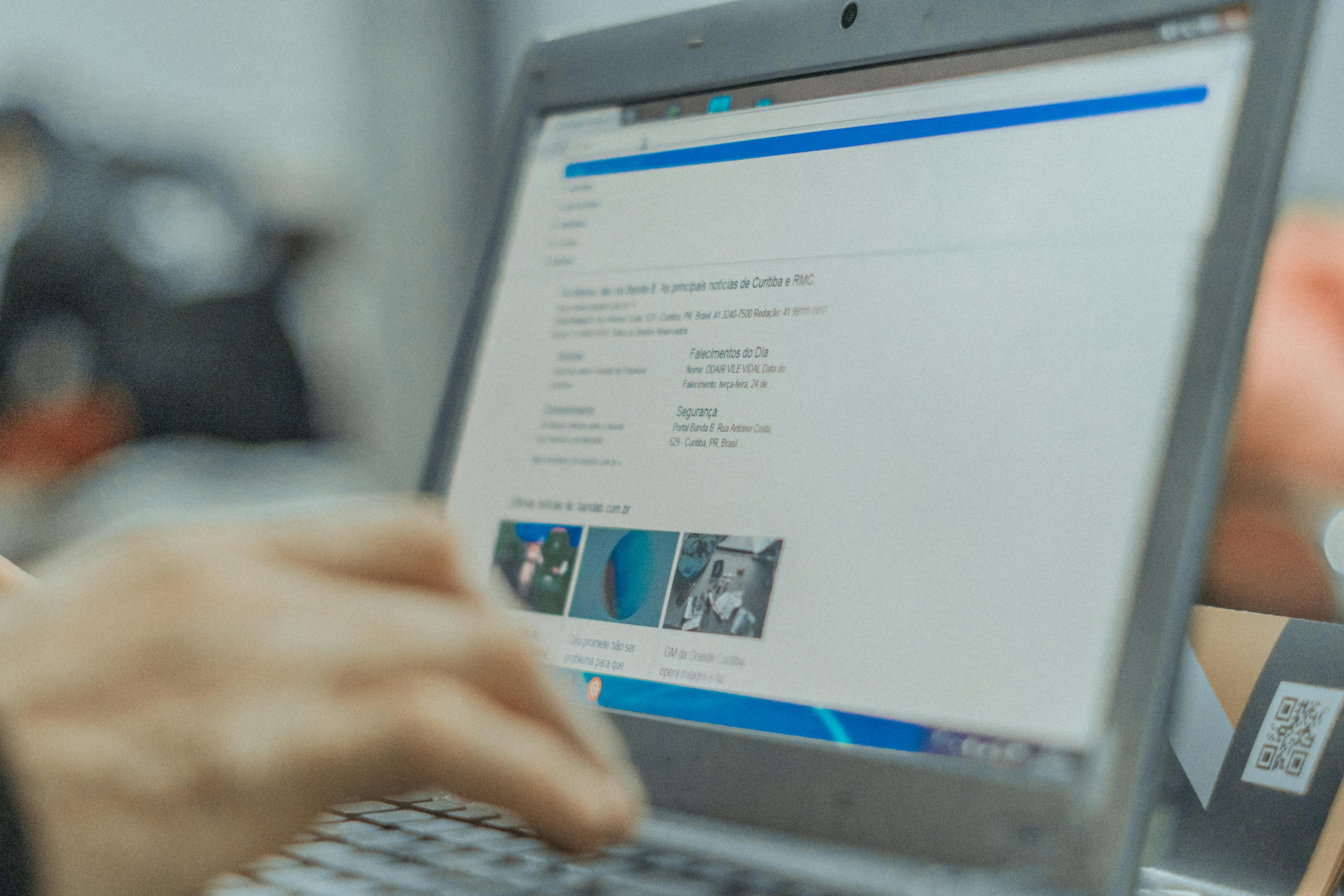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