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代史学较之传统史学更趋复杂,古今之外复有中西。王先生多次提到史学之分、学科细化的问题,著作与伦理分作二途,在西方化的笼罩性影响下,身处于“中西两辆相向而行的列车之间”的不同学者,各以其立场论史。柳诒徴曾说,“古人之治史,非以为著作也,以益其身之德也”,近代的新派学者论史学往往发扬其中“疏通知远、属辞比事”的一面,试图以传统中的记述之学贴合现代客观的、科学的史学,对于史学之于“为人”一面往往忽略(《国史要义·史德》)。从史学而论,在近代西学的冲击下,传统史学混搅一体的“价值”与“事实”被整齐地割裂开来,史学亦被削弱了本然之价值。因此,在近代变动之际,史学的现代化是一条清晰的客观化线路,而在“胜利背面”却暗含有另一层申述价值的趋向,就像讲座主题陈说的谭嗣同、王国维、刘咸炘为人所忽视的面向。
关注“消耗性转化”,便是从转化的过程之中,寻访那些受现代“价值”、话语、思维体系影响而隐退的潜流。但值得注意的是,“重访”并非“打碎”或“革命”,就像王先生在讲座一开始所声明的那样,“绝不是要复古”。因为许多近代东西方的“思想武器”进入以后,确然将很多过去习以为常而不自知的历史发掘出来,像“君史”与“民史”、公例与进化,乃至争论不休的历史分期论等等,皆为当时审读历史提供了必要而有益的视角。但是,“进步”“转化”带来意义,并不等于淡化、遗忘的潜流不再具意义,更何况身处于历史场域之中的个体皆为“有限理性”,不能夸大“历史理性”,而忽视转化所具有的或然率,暗示着人类思想的其它可能。
以我浅显的理解来看,“重访”的要义乃在于“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避免落入“本质化”的窠臼。因为“价值”重建下的事实,若未经“重访”则往往使人误以为其本来如此,而忘乎古人所经历的选择与转化过程的消耗。“重访”的最终目标或近似于附录《时代关怀与历史解释》中提到的“一种尽可能想重建客观史实的前提下、具有分寸感的实践”。或言之,“重访”“重审”并非是做“翻案文章”,而是重新发掘边缘的、消耗的思想与文化,继而探究某一时代的不同思想、政治、文化之间如流丸互触般的交互影响与演变,并且将这些重新发掘的思想资源纳入今日思想的仓库之中。
重新阅读王先生的演讲录,似乎也感受到“重访”的不同层次,除了作为“个案”的“重访”,也有现时研究的“重审”。“风”是刘咸炘阐释历史的一种方式,但对于王先生而言,这一命题非只适用于刘咸炘,现代人不仅可从其论说之中获取一种了解历史的途径,还须“用现代的学术观念和语汇去深入阐述‘风’的各种复杂的机转”,甚至是用此一度被遗漏史学观念来扩充对历史理解的新的可能。
人文主义与历史心量
有次与师友闲谈,席间有位提到,听王先生讲演常常会有一种感触,即无论原本知或不知其谈的知识与思想,却常有一瞬之间点亮心间的感觉。闻者皆深有同感。对此曾思忖许久,“重访”之际似有所感悟。
演讲中王先生曾几次谈到皮埃尔·阿道的《哲学是生活的一种方式》,并称之为同道。“哲学是生活的一种方式”,说明哲学本有其日常生活的面向,而在几度抽象化之后才成为纯粹的思辨。后来王先生著有《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也同样探讨思想史上的“生活性”。对于思想性与生活性的探讨,在我看来,或许是对近代以来“分”的历史学的一种有分寸的“合”,也是一种恢复思想“本来面目”的方式,是打动人心之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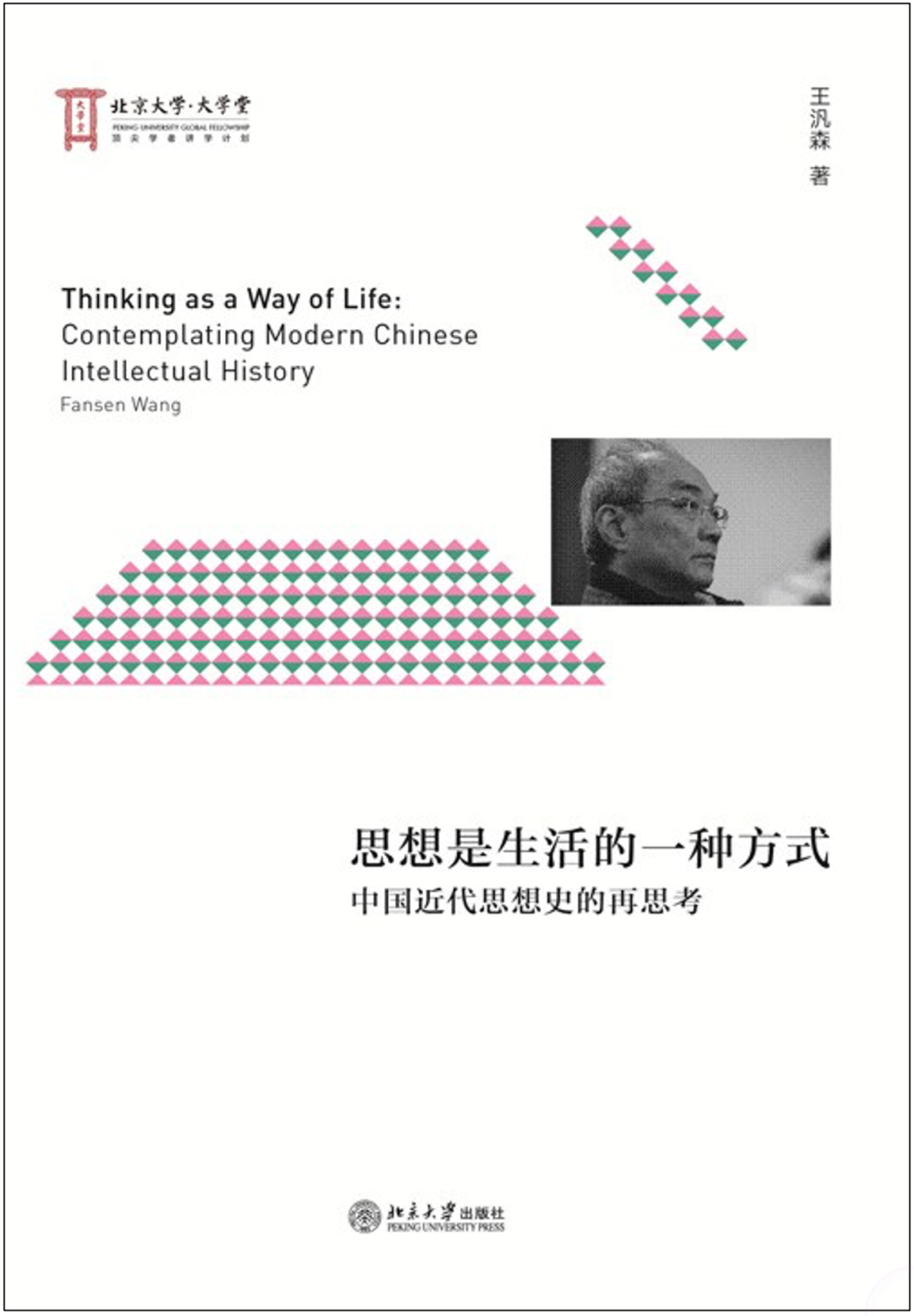
王汎森著《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
在《执拗的低音》开篇,王先生提出过“‘学’是什么”的问题。新的学科建立之后,新的知识、理论涌入,重构了人们的认识框架,仿若是新的聚光灯照射在旧材料上而展现出古人所未见之面貌。可随之带来的问题是,传统中往往包裹于一体的学问、道德、信仰、意义、价值被裂解开来。
从传统史学来看,过去与现实、未来相连,当下的现实问题与历史的普遍道理相通,就像苏洵在《史论》中所言,事、辞、道、法,史可兼而有之,文章、法则、义理与史实本就混为一体。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就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王夫之的看法谈不上高妙,却颇具代表性,其对史学的价值、史料的用途的见解几乎与近代重视客观记述的史学思想截然相反。在王夫之看来,鉴往知来是史学的核心价值,这种思想无疑有着应对现实的“生活性”面向。
可是近代史学的强风拂过,原本多元的史学历经“去伦理化”过程而“消耗性转化”,传统史学中暗含的历史与现实关联被切断,历史只是历史,不再具有所谓法则、义理的价值,也无需寻觅什么“效法之枢机”。增订本新增日文版序言中,王先生特别提到了当下的“历史意识危机”:“那时候感觉过去的历史与我们的生活是可以有同代感的,但现在感觉好像什么都不相干……现在已经越来越难回答,历史跟我们的社会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从理论的发展而言,历史学的现况固然可以从后现代主义的崛起、相对主义盛行等角度阐释,但问题的分析并不等同解答,如何应对历史意识的危机,几乎贯穿了王先生整部书的思考。
在王先生看来,发掘“低音”可以说明“人文的多样性”,复现历史上的多元、丰富的可能性,“人类的经验并不只有这一刻才是对的,或是只有这一刻才是最进步、最有价值的,过去可能也有我们可以取法的资源,而且未来也还会再改变”。王先生似乎在论说历史的同时,试图展现价值、道德与学问探索并非必须割裂,历史与现实更非毫不相干。他在书中曾提到“存真实以关联呼应现实”的主张,认为史学可以同时存有二义,一方面是尽可能重建史实,另一方面是“关联呼应”时代的表述。从个案层面而言,这揭示了陈垣、陈寅恪史学中为人忽视的一个面向,从研究层面来说,则有着由“史事”而及“史义”的价值。从此角度来说,学问不止是学问,史家关怀、时代境遇与史学工作不仅在被研究者身上套叠,也同样叠合于研究者身上。
近代百年史学发展,将原本统合一体的史学渐而“隔”为数部分,史学限缩于封闭的“经验空间”之中,好像熊十力所言矿物质化的学问一般,成为陈列的展品而失去其本身鲜活的价值。然而王先生通过对历史多样性的探索,原本因史学客观化而割裂的过去与现实,借由“关联呼应”而重建连接,在忠实建立史实基础上又充分展现出历史的人文特性,重新将知识、经验与“人的尊严和主体”有机结合在一起,历史仿若重新成为人生、当下的一部分,成为走向未来期待的经验场。这不仅是一场人文主义的试验,同样也是一场“知行合一”的实践。
最后,谈一个个人阅读的感受。我时常觉得王先生的研究有“说理”之感,所言为“史”,又总含有某种“理”,直到前些时阅读《历史是扩充心量之学》时,其中一段话或许可印证我的感受,也可用以阐明“重访执拗低音”的意义:
所谓“扩充心量”可以理解为心中天生便具有众理,应如大厅中由千灯组成的吊灯,每穷一理,便开启其中一盏小灯,读书穷理,基本上是使人心原有的各盏灯(众理)获得开启。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