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2023年,多次受伙伴机构之邀,我跟随不同团队前往丽江老君山黎明乡开展实地调查与学习。
老君山可读、可学习,它诠释了自然、地方、景观与人类生命、社会生活的复合关系。它被当地人视为神山,却并没有被过度神圣化,其自然性未被全部抹去,它首先是众生与万物共同存在、相互塑造的场所。
老君山地处喜马拉雅东南缘横断山脉三江并流区域,属云岭一系,头尾紧连着白马雪山、玉龙雪山。它是冰与火的遗迹。从浅海到高山,它慢慢隆起。大地断裂之处,正好被江河切割开来。

老君山黎明河流域,当地傈僳族人所称的“巨谷始祖”——诺玛底,人居沿深谷散布
在金沙江流域纳西、白族等多个族群流传的神话故事里,如今位于老君山两侧的金沙、澜沧两姊妹曾一路南行,为追寻爱情,逃离了天神爹妈的束缚。她俩在石鼓古湖分手,一个继续往南,一个向东。东去的金沙姑娘切开玉龙、哈巴两兄弟的封锁,挥洒而别,留下了被斩去头颅的哈巴。
河谷地带,人烟聚汇,气候由湿热变得干热。冰川和雪峰隐去,大象与犀牛南奔,普米族神话中化天地、造江河的神兽——古湖旁麇集的马鹿已遁于山林。
金沙江流域由昭通、曲靖、昆明至丽江一带曾多处发现有更新世晚期(距今约3万年前)犀牛化石。樊绰《蛮书》等文献称南诏产犀甲,如今云南多地还保留有犀牛洞、犀牛塘等名称。
化名“华春”的老一辈生物学者曾在《云南林业》1984年第六期报道,“根据群众的反映和实物的证实,思茅地区菜阳河保护区的热带森林里,1933年还有一对犀牛在活动,但不幸在当年就被猎人所捕杀,当地群众至今还保存着犀角。而在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的密林里,当地群众在1939年前还见到过犀牛,遗憾的是,自此以后,犀牛便无影无踪了。”
近两千年来,云南生活着苏门犀、印度犀及爪哇犀3种,约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消失(何晓瑞:云南历史上梅花鹿、犀牛和赤颈鹤的分布及其绝迹原因的研究[J]. 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94,16[3]: 295-298)。这两千年,由于人口剧增,毁林开荒种地,围湖围泽造田,不少动物失去了生存环境,许多大型兽类、鸟类被人类猎杀绝尽。
多重身份:老君山的时空压缩
这一天,我们穿越金沙江河谷,在压缩的时空里,多种异质观念和实践相遇在黎明——傈僳族人的家园。
老君山,长期处于多种强大文明的边疆,是文化交织的现场,也是各自的缓冲带和结合部。循山河而来,各类型人类文明共生其中。有剑川古人称它为“滇省众山之祖”,以太上老君的变化之名施加其上;但存在更广泛,且迟迟未变的,是众神众生同在的传统生态文化。
远方的太上老君,似乎并不知晓这偏远的山水,哪怕今人附会以老君炼丹、千龟灵聚等意念。当地世居者也没把这外来的神仙特别当回事。他们敬重性灵,习惯了在洪水朝天和独脚妖怪肆虐时多次拯救人类的青蛙舅舅相伴的生活。
从海拔1828米黎明河汇入金沙江的岸边,到海拔4515米的老君山最高峰——金丝玉峰,有石器时代以来悠久的农作历史,有高山、峡谷游牧的岩画遗迹,有诸葛亮渡泸水、南诏吐蕃铁桥之争、元跨革囊、红军长征过金江等多种符号的深刻印记,有傈僳、普米、纳西、白、彝、藏、汉、回、傣、苗等多民族的现实生活场景。落差巨大的垂直海拔地貌里,由低到高,从春到冬,从草本到灌乔,数不清的花朵次第开放,为众多昆虫的口粮所需提供了多种多样的蜜源。
丽江老君山黎明景区,以面积约250平方公里的丹霞地貌为主体,大致为黎光、黎明两行政村的地界。而更大范畴的老君山还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地质公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世界级自然遗产等多重身份。
除了国家到地方的管理系统,当地还有社会组织长期协同社区推动的“老君山社区可持续发展与生态保护”,黎明、黎光有社区保护地(涉及集体林、黎明河流域),以及村寨银行等为基础的社区行动。
这样的实践,往往行走在各自的轨迹上,彼此缺少交集。多年来,科研院所、民间研究者、企业等对老君山的探索和开发从未停止,但社区参与度不高,对其成果并不了解,也很难感知由此带来的影响。面对当地人古老的记忆和诸多社会行动的积累,我们该怎样获得对地方整体的认知?
传说:民间的意义构建
黎明一带,曾经原始森林遮天蔽日,野兽肆虐,虎和熊是其中的王者,豹狼、野猪与猿猴几十年前仍不时光顾村寨。
当地傈僳族人迁徙至此居住的时间并不久,自称仅二三百年。他们零星散布于山间,在森林中标志性的“刀耕火种”——游耕、游牧、渔猎、采集的生活方式直到近现代才发生巨变,人口也从这一时期开始增多,进而形成了市集——红石街。由此可以翻越老君山,去往兰坪、维西,经过湍急的澜沧江和累累白骨堆成的碧罗雪山垭口,是怒江、独龙江……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的阳光照到这里,因此也有了黎明、黎光的村落命名。两村境内,有道道深嵌的裂谷和高耸的红色砂岩,傈僳族人称它为——“大地之神用自己的身体补地之所”。它的风景早已闻名于世:中国最大规模丹霞地貌、世界级攀岩圣地、三江并流区域生物文化多样性代表性地区、亚洲物种起源和分化中心之一。
它被称作“太阳的故乡”,有人认为不过是为迎合旅游业发展而新造的传说,但不幸已经在当地傈僳族人之间流传,几乎成了信史。所讲述的是,现居黎明的傈僳族先辈在迁徙过程中说道:“太阳落下去的地方,是太阳的故乡。我们要到那里去。”当他们来到黎明,发现这里一日里太阳三升三落,就认定此地即太阳的故乡,于是便定居下来。
怀疑者指出,根本没有一日里太阳三升三落的现象,这地方山高谷深,阳光每日直射的时间较短,冬至时短得只有三四个小时。“太阳故乡的传说,是假的,编造出来的。”可是,哪一个故事没有在流传中被改写、移植、借用或转化呢?大地之神如此眷顾这里,剖开五脏六腑,留下满目的红色巨石,这故事又该从哪里说起?太上老君何时驾临?山下的金沙江水,可曾载着孔明先生南来?
“疑古”,谨慎对待原始资料,是学习者、研究者应持有的态度。但对于文学、文化而言,传说、故事与神话,是民间自主的意义构建、表达与认同。对历史的重新整合与诉说,让记忆从虚构中释放出来,从沉睡里醒来,成为我们认识老君山,认识黎明的渠道和载体。就像寻找一把文化的钥匙,一条文明的线索。我们期待听到更多神话、传说、故事。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值得认真对待。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匮乏,帮助我们接近当地人的灵魂,触摸其血脉,理解其最初的、历史的和当下的生活形态,以及他们的智慧。

被观看的黎明傈僳族人
攀岩:文化激荡或擦肩而过
老君山黎明富有被国际国内攀岩运动者追捧的Indian Creek式岩壁。从2010年首批线路开始,Mike Dobie、Cedar Wright等先后在这里开创了超过200条难度级别在5.13-5.5的线路。有一处为中国最大的运动攀岩墙,Mike Dobie将其命名为El Dorado(西班牙传说里的黄金之城),有人猜测它也可能是亚洲最大的攀岩墙。

攀岩者上方可见岩蜂巢穴,黑色痕迹或许就是傈僳族人烟熏火燎采岩蜂所致。网络资料图
盛名卓著的攀登基地,却与当地人的生活没有多少联系。在时尚的运动中,地方不见了。对多数村民而言,就是一群外国人,住在这里很长时间,经常攀爬,然后有公司经营,大量游客来体验,如此而已。
当地傈僳族采岩蜂的古老技艺,被严重忽视了。
这种展现在悬崖峭壁、高大树木上的绝活,以“蜂氏族”(Beit Pat)最厉害。
傈僳族各氏族多以动植物、自然现象作为称谓,有虎、熊、蜂、鱼、猴、羊、雀、猪、鸡、耗、木、荞、麻、犁、霜、火等。黎明傈僳族人认为,蜂、鱼是附近各氏族中的老大,敬称为“阿底布”(A Di Bu)。由此,我们可粗略判断出傈僳族在森林中的原初生活方式。而蜂氏家族里,又有蜜、糖、叮(因蜂蜇而名)等姓。糖、叮后转化为唐、丁。
蜂氏族祖祖辈辈养蜂。他们的眼中,蜂类有土蜂、岩蜂、马蜂、黄蜂、葫芦蜂、土甲蜂、赤眼蜂等多个品种,彼此之间也有相亲相杀的故事。
傈僳族人寻找野蜂,方法奇妙。
捉上一两只蚱蜢、蜻蜓等昆虫,或割一小块肉,固定在细棍上当作诱饵。
预备一根长头发,一端打上活结,另一端拴上白色的火草绒毛或鸡毛等分量很轻的白色标志物,用来引导追踪。
拿着绑有诱饵的细棍在林间舞动,引来野蜂啃食。
瞅准时机,将头发丝套在蜂腰上。
野蜂将诱饵啃成接近花生米大小的肉团后,将其抱起往蜂巢飞。
捕蜂人跟着一路撒腿就奔,或攀上岩石、大树张望。
由于吃饱了一餐,带上了食物,野蜂的灵敏度和飞行速度都慢了很多。
捕蜂人跟着标志物追啊追,看落在什么地方,就能找到蜂窝的准确位置。
火烟熏烧,驱赶保卫者,迅速用一块布包裹住蜂窝,然后用刀割下。
蜂窝取回,系在房前屋后。从此,野蜂变家蜂。
采岩蜂是这样的流程:
仔细观察,看中了高高崖壁上的蜂巢。用那宝贵的铁钎和铁锤,在崖壁上一点点凿出一个个洞眼。
“我们傈僳人可能是最早发明膨胀螺丝的人”,黎明乡文化站站长李文林说,“就当是个玩笑。但傈僳族人想到的办法确实有这样的效果。洞眼外小里大,先钉进短木塞,再用楔子加固,最后是木桩。任你使多大劲都拔不出来。”
就这样,极耐心地花上半个月,一个月,甚至两三个月。期间再准备好麻绳,甚至好几天住在山洞里的伙食。慢慢地,采蜂人一点点接近蜂巢,终于能够收获蜂蜜、蜂蛹和蜂蜡。
岩上、树上坠落的采蜂人不少,被野蜂蜇死蜇伤的也不少,也有傈僳族人神奇的药物治疗获救的地方传奇。
这技艺真了不起,但更了不起的是傈僳族人对大自然充满敬意而尽可能少量地索取,乃至以身体以心灵回报。可惜,我们拜服于现代文明,常常忘了这饱含生命意义的传统存在—— “自然人”,及其自然方式。如果我们尝试去进一步分析,找野蜂、采岩蜂,将会呈现出傈僳族人所建立的一套地方文化符号、功能和意义体系,它包括且不限于以下多种元素:景观、山水、动植物,森林与家屋、社区、族群,男与女的身份、分工与协作,劳作与休闲,交换与分享、馈赠……
河道清理行动引出的三个问题系列
山有山神,地有地灵,树有树魂,水有水仙……
黎明傈僳族传统遵循十月历法——被称作“花鸟历”,一年划分为花开月(3月)、鸟叫月(4月)、烧山月(5月)、饥荒月(6月)、采集月(7、8月)、收获月(9、10月)、煮酒月(11月)、狩猎月(12月)、过年月(1月)、盖房月(2月)。
“花开了,三月春回大地;赶牛来啊,把地犁了;花开月哟,花开月;
鸟儿叫,蜂子飞,人间四月已来到;春雨里啊,把田耙了;鸟叫月哟,鸟叫月……”
他们有不少关于水的禁忌,如不能往水里大小便,不能往水里扔石头,不能用木棍搅动水底,以这些看起来细碎、严苛而执拗的信念长期保育着生境。
直到今天,他们仍然依靠观察物候来指引生活。黎明河的青蛙、知了叫了,意味着雨季就要到来,是时候开始播种,“知了叫,要翻地;樱桃熟,种苞谷”,“青蛙一叫要下雨,鱼儿跃水要涨水”。

近年来,黎明乡境内多发洪水。图为2021年“819洪灾”情况。8月18日起,持续的强降雨导致黎明河、美乐河暴涨,农田、道路、房屋等不同程度受灾。 (丽江先锋网)
2021年8月,老君山迎来频繁的雨。
黎明景区L公司为保护企业财产,花了数万元清理河道,并将一些巨石移走。8月19日,黎明河暴涨,水位最高时,距该公司建筑物地面仅10余厘米。洪水泄过,下游有大桥被冲毁。公司员工直呼“好险”。
企业财产保住了,但与此相关的代价是什么?上游清理河道,是否加剧了洪水的流速、冲击力,导致下游受灾?
L公司应对洪水的措施,地方政府、国家公园及社区各有不同看法。
地方政府认为,L公司擅自行动,破坏了黎明河流域管理的规定;国家公园管理局认为,L公司的行为超越了其经营范畴、地理界限,有损河流生态。在我们的调查中,有数位村民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巨石能够调节水流,减缓冲击,而河道去弯就直,并不利于防洪,鱼蛙蛇等动物会失去它们的家,人们干农活也会失去伙伴;此外,巨石成就了黎明河的美,是地方生活与景观的一部分,应受到尊重和保护。
回过头去梳理,一场洪水危机的应对,有不少问题值得探讨。
问题系列一:
L公司事先如何征求各方意见,以求达成共识?L公司建筑物所处地理位置对河道及行洪有什么影响?L公司是否有权清理河道?该如何清理,怎样避免破坏河流生态及地方文化?除了清理,可以采取别的什么办法?黎明河流域管理有哪些方面的事务需要加强?

黎明河
黎明、黎光村民十分注重保护和恢复黎明河流域的整体生态环境。黎光村11个村民小组,除去一个户数较少且零散分布于国有林场范围内,其余10个均建立了各自的社区保护地,就森林及林下资源、水、鱼类及其他野生动物的整体保护达成了共识,且各自制定有具体的奖惩、管理措施。
黎光村村民介绍说,黎明河中有不少特有的珍稀鱼种,其中一种叫竹根鱼(硬刺松潘裸鲤),因形貌似竹根而得名。过去一个时期,自然河流受到越来越强烈的人类活动干扰,且常有偷钓甚至电鱼、炸鱼、毒鱼等滥捕现象,导致黎明河鱼类数量逐年减少,竹根鱼基本消失了。旅游业的发展和村民生活的改变,使得河道里各种垃圾越积越多,塑料袋、酒瓶子、易拉罐等,严重影响了河道的水质健康和环境景观。

硬刺松潘裸鲤 图片来源:长江文明馆
于是,黎光村沿河各村民小组决定联合起来,达成共识,推进流域保护。村民认为,沿河社区,只要有任一河段的村民小组未启动保护措施,就算其他小组开展行动,垃圾污染、捕鱼问题仍将难以管制。经过长时间的反复商议、协调,2016年起,10个沿河村组全部加入流域行动,涉及河道卫生改善、垃圾处理、全面禁渔,以及青蛙、水蛇等其他动物的保护等,全线联动,共同实施监督和管理。
近年来,竹根鱼又重现黎明河。社区行动引发了我们对河道清理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它需要遵循什么样的地方文化逻辑?如同关于青蛙、知了的谚语,它凝结为当地人的共同认知,不仅告诉人们不该做什么,指导人们该做什么、怎么做,还预示和解释了其他人要做什么、说什么。
问题系列二:
在社会、经济行动之前,文化调查如何先行?谁是地方的主体,是谁的调查,谁参与调查?文化调查需要获取什么信息,怎样获取,提出什么主张,以帮助人们采取更恰当的行动?如何改变发展者获取、认知及利用地方知识及信息的方式?行动过程中,如何避免当地人失语?当地人处于怎样的社会关系中,存在不平等、边缘化和权利被剥夺的状况吗?
洪水危机,河道清理,是一个在地的真问题,其最优解决办法也只能是在地的。
只有对话,形成互动,才能激起社区的内生力量去真正解决问题。这不是权力的让渡或给予,而是相互赋权的过程。整体性视角让我们明白,任何观念与实践都与文化中的其他方面有所关联,任何文化所承载的社会生活都与所在地域的其他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洪水危机应对的策略产生、行动实施和信息反馈,回到了它的起点:怎样看待地方、当地人,如何认识地方、当地人?
问题系列3:
什么人,什么东西,什么地方构成了社区?社区有什么样的不同需求,不同权力类型,以及可见的不同利益场景?什么是社区福祉?居民的幸福感从何而来?个人或某一人群的社会责任、社会效用是什么?怎么实现?如何看待公共性?如何增强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和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怎样建立公共事务共商共议的对话机制?如何促成共同的行动?社区在这一过程中拥有什么身份,哪些权益,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可以有什么贡献?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如何实现创造性参与社会行动的愿望?
行动:一种文化比较
一系列并未终止的问题,正是学习的开启之处。而我们更关注:当地人怎样看待生态环境,如何认识其价值和意义?当地的生物多样性与地方知识彰显了怎样的人地关系?
傈僳族人拥有万物有灵信仰下人与自然的互动行为和生存哲学,这是他们在漫漫岁月中与天地朝夕相处得出的智慧。我们正可以借鉴,以此丰富内心,验证自己的生活方式、观念,指导自己的行为。
“我们住在山上,从来没有让山林受到损坏
不撬大石头堆,粗壮的大树我们不兴砍
去到白云环绕的雪山,攀满青藤的古树枝不兴折
去到树林,大杉树不兴砍来盖房子竖柱子
大箐沟里的青竹不兴砍,捡些枯竹子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的村子就在山林边上,所以不会去破坏它
不光注重山,还注重水啊,草啊
我们住在水边,从来不捅水底
不去破坏水神居住的大河与水源
平时我们在山坡上干农活、放羊子
不会让山神受到惊吓
山里的山货,蕨菜啊,菌子啊,野菜啊,不兴过多摘回来”
……
老君山的风景,离不开千百年神性的守护。从不过度惊扰自然,而是保育生态,维系可持续的生活。具体而微的观念,一个个生命、性灵,让我们认识到当地文化的大同和与众不同。这正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不同文化之间有什么相似,有什么不同?为何相似或不同?可以从中获得什么经验?
尊重差异,并乐在其中。通过建立与当地人沟通的渠道,发现不同人群潜在的利益冲突,使行动有公平的决策。基于此,针对地方的问题和需求做出回应,并将自我和需要帮助的人群、个体作为同一目标。
我们因为他者,因为所能触及的事与物、思想与观念,确定并衡量自己的存在。而周遭一切,在某种程度上都有我们参与创造的痕迹。当离开时,我们可以说,有些东西已经附着在自己的身体与观念之上。风景能够穿过记忆,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或多或少,它都能支配我们的生命,为我们的日常行为提供动力。风景是流变的,从一个时空到另一个时空。
(本文是调研报告《山河影:金沙江中下游流域环境记忆》的第四篇,有删节。报告由自然之友玲珑计划资助。社区调查得到了乡村之眼乡土文化研究中心[From Our Eyes]、梦南舍可持续发展服务中心[MNSC]、丽江健康与环境发展研究中心[H&E],黎明、黎光、喇嘛寺村民的协作与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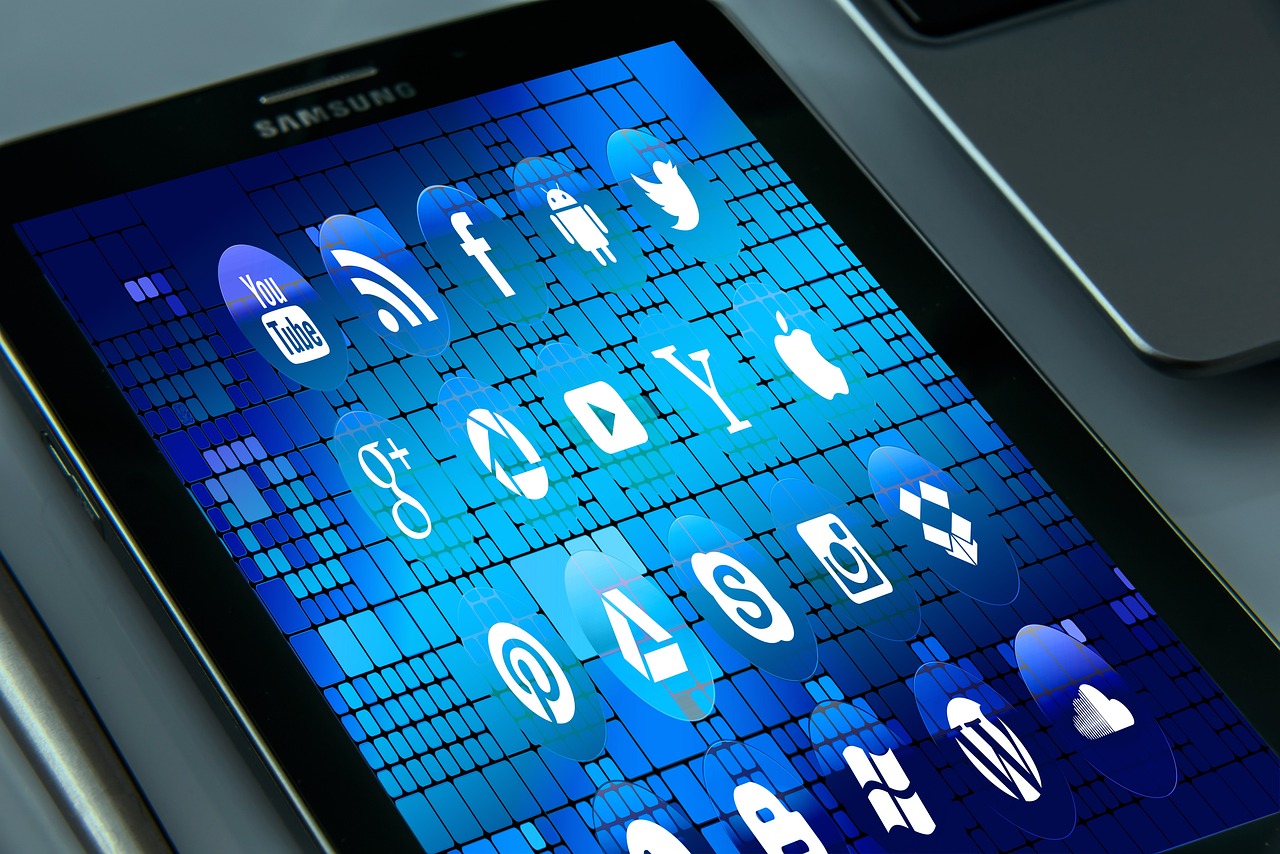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