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躺、佛,越来越成为一种流行词汇。是无病呻吟,还是日常现实折射呢?布尔迪厄说过:“只讲生存条件的深重苦难而排斥其他一切困苦,无异于对很大一部分反映社会秩序的困苦视而不见和不理解。无疑,社会秩序已经使大苦大难有所减轻,可是社会分化的过程中,社会空间大大扩展,从而制造了助长各种日常困苦空前加深的条件。”
《生活在低处》就是这样一本书,其重点并非在于叙事或评论,而是让自己成为口述史范畴的被写体——在不断的自我剖析与审视中,呈现时代的个体镜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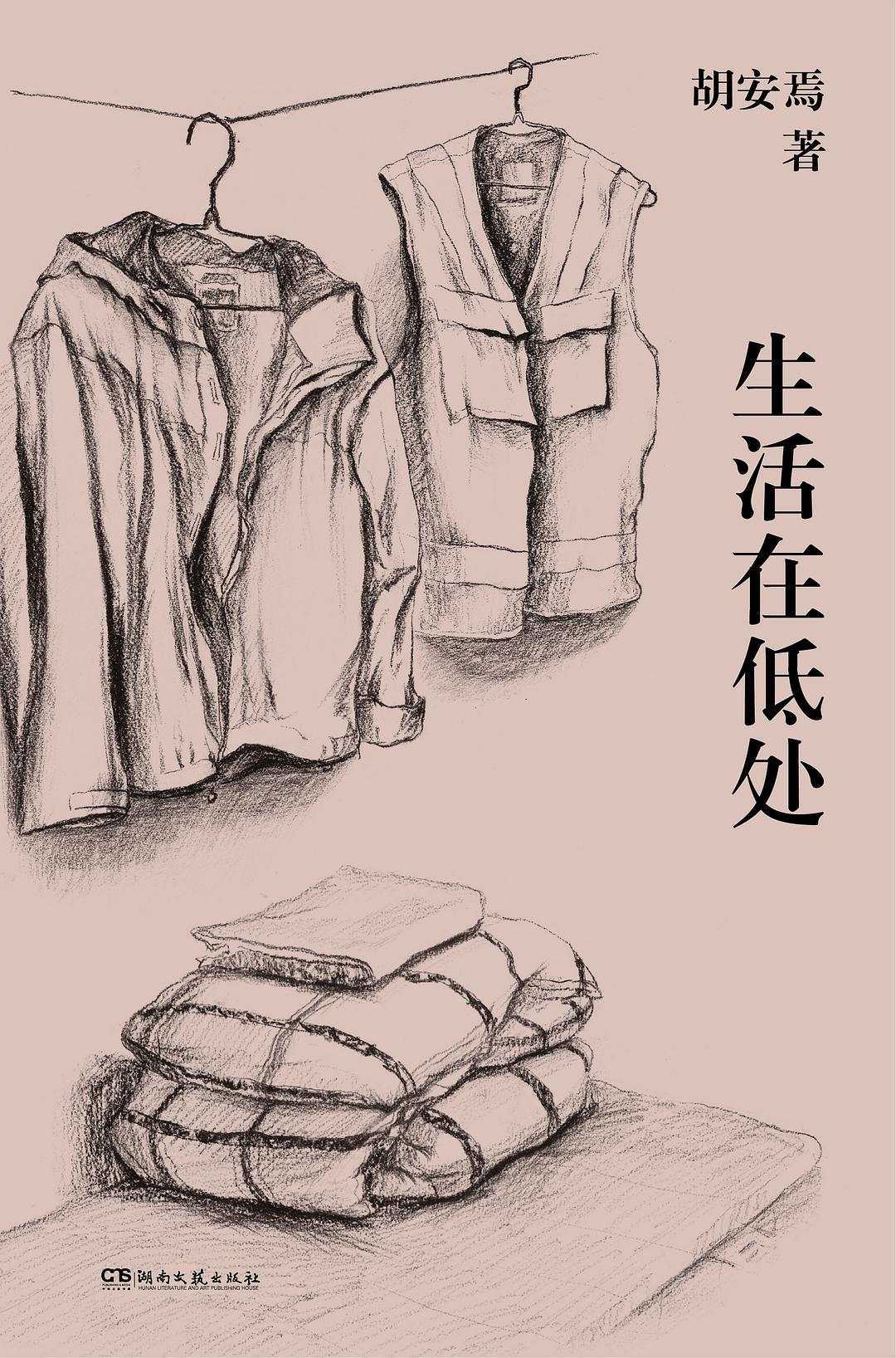
《生活在低处》书封
过于表象化的丧
在书中,胡安焉记录着或大或小的无奈,好像是走不出命运安排的楚门。然而,周遭事物的微小反常,则会触发他作为写作者的观察与思考本能。
全书分三个篇章,依次为“童年,暨我的家庭史”、“我为什么写作”、“活着,写着”,让读者像是循序走进了作者的客厅、书房与楼下的菜市场。
在“童年,暨我的家庭史”,父亲被校园门卫误当成盲流而拒之门外时,他作为儿子的本能不平及无可奈何的释怀;作为“黑五类子女”,“在迫切地想要获得安全感的心理推动下,母亲只有更加表里如一、全身心地信服于那更高的主张”......
三个篇章,并非完全割裂。在“我为什么写作”,胡安焉又再次提及母亲——“父母没读过我写的任何东西,我也从没打算让他们读”,但是母亲会“专门去书报亭”买下有作者署名习作的杂志,并“把它像宝贝一样藏在抽屉里,还一藏就十几年”。作者自嘲道“或许直到看见为我取的名字被印到了杂志上,她才终于为生养我这件事感到一丝欣慰”。
有别于学院派叙事的克制,他始终将各种思考贯穿在叙事之中。在胡安焉看来,“父母如何看待生活和社会、他们相信和遵从些什么,以及对待我的感情形式等,都极大影响了我的性格、气质和追求,这些与我后来的社会经历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今天的我”。
他一再强调:和绝大多数人一样,我只是一个普通人,至少在四十岁之前,做过的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工作,经济收入还拖了人均收入的后腿;从来没有人用“优秀”来形容过我,也没有人真正关心我的内心世界。
这让我想起“沉默的大多数”这一传播学理论,也说明胡安焉的走红并非意外,而是有种鲜明的社会属性与现实意义。在书中,他曾试图总结自己写作的“导火索”,诸如陌生村妇讨要他的饼,邂逅“疯女人”顾客,与电动车骑手的“路怒”争执,让他愈发“变得敏感和脆弱,同时又易怒和歇斯底里。过去我不在乎的一些事情,如今却变得非常在乎;而另外一些我从前在乎的事情,这时却变得不再在乎了.....可是孤独地在漫无目的中摸索,我又害怕被那虚无的深渊吞噬。无论是什么,我希望有一件事情,是我可以投入其中,同时又不必为此和我厌恶的现实打交道的”——像胡安焉在“我为什么写作”部分写道“那些经历在发生的时候,我是像囫囵吞枣一样咽下去的”、“卡在我的喉咙”,“我要反刍这些经历,就得先把它们吐出来”,“我的写作是渴望交流的”。
这种感受,用流行的词来说或许是“丧”。但我觉得“丧”过于表象化,就像所谓“转型阵痛”的说辞一样,对背后的现实意义有所消解。这些年来,《钢的琴》、《Hello!树先生》、《年会不能停》等电影引发的热议,都是现实的戏剧化折射——宏大叙事与风和日丽之外,每个时代都有着沉默的大多数,其作为小人物的丧抑或憋屈,需要倾诉与“共振”。
在这个时代,我们往往可以随口说出自己关心的时事热点或名人八卦,但对于我们所在城市的日常却缺乏共情能力,而这种“缺乏”又进一步加速了人际之间的疏离,以及个体的孤独、愤懑甚至憋屈,有种近乎宿命的桎梏感——就像《毕业生》片尾的长镜头。
“为旧鞋子惊讶”?是意识悖论
胡安焉在“我为什么写作”部分继续写道,“文学如今已经失去了大部分读者,甚至文字载体本身都被新的内容载体挤到了边缘......我也几乎不阅读”。
他曾在这部分字里行间反复探讨“虚构”、“非虚构”这两个写作方向,以及与自己写作风格的匹配度,但在我看来,“非虚构”始终是胡安焉的底色,这种底色给他带来的“馈赠”甚至超越了他作为写作者这一身份的局限,也由此具有了更普遍的现实意义。
胡安焉经常喜欢提及美国作家卡佛的名言:“作家要有为普通的事物,比如为落日或一只旧鞋子感到惊讶的禀赋”。在《生活在低处》这本书的“活着,写着”部分,这种禀赋是有所体现的。例如,胡安焉和朋友去理发时,理发姑娘与其朋友的争执,能让他意识到“她那凶神恶煞的外表之下,确实藏着一颗感人的少女心”;夜晚从店里回到住所,与房东家看门狗的夜晚对视,既有人与动物之间的交流渴望,也有他作为社会人的各种纠结或自我审查;在街心花园看到一只“比熊”,它对于一处寻常水塘的雀跃,以及被不解风情的主人无意间拽走甚至勒伤时,作者带给我一种借物喻人的惊艳,甚至有些意识流的意味。
全书不容错过的是第三部分之中《内心记》这章,这部分看似散碎,却颇为“结案陈词”的意味——胡安焉置身自设的文字结界,陈述“高姿态”的初衷、“工作”的价值,像唐吉坷德一样冲着风车挥动长矛,而“风车”在这里则是外部世界与其内心世界的共同体。其看点如前所述,并非诠释“外部世界”或者对“内心世界”进行哲学化的升华,而是有着他根植于自身经历的“偏见”。用他的话来说,这“我意识到自己与现实的对抗往往是表演性的,有时甚至是矫情的。但那又怎么样,这仍然比流俗好,而且我有相对清醒的自觉意识”,“真理并不和偏见对立,相反,真理是所有偏见的总和”。
在一些所谓精英的世界观来看,往往会傲慢地混淆“流俗”、“普通”、“大多数”等词汇的内在区别,甚至将这些有意无意的统归于粗鄙,从而更多形成割裂、错位,就像教科书里提到五四运动时,知识分子问工人同胞“生活丰不丰富”,有一腔热情的词不达意。
通过胡安焉对“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种种琐语,可以看到“流俗”是随波逐流、是盲从,让他警觉却也困惑,他写道“如果没有了那块石头,西西弗斯会获得自由吗?......徒劳地承受无止境的重负,或坐下来面对虚无的痛苦,两者中哪个是更优的选择?”
回到这部分开篇的思考——“文学如今已经失去了大部分读者”,究竟是文学的问题,还是文学界的局限或偏颇,就成了另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诚然,文学写作是个体行为,不必先天地承担所谓社会责任或者社会功能,但是当各种文学大奖带给普通人的“个体共振”越来越少时,胡安焉这类写作者能够被热议,显然填补了当前文学界的缺失部分。这种缺失,并不是靠一种新的世界观或者人生观、价值观来填补,反倒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引发社会轰动的“潘晓来信”,这本身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能够以现实、诚恳的笔调呈现就已是难得。
由此,作家卡佛提及的“普通事物”成为一种悖论。如何界定“普通”与“非凡”?在我看来,“普通”作为一种指代或处境,反而是一种让人共情的现实镜像,这就像该书读者常见的反馈——“敏感又真诚的人”、“了不起的自我察觉”、“唤起了自己的阅读体验和记忆”。
胡安焉在《生活在低处》写道,“如果我们的慈悲不能像钢铁一样坚硬,我们将贫瘠得只剩铁一般的原则......其实我也爱生活,但我不爱你们的生活,而你们总想否定我的生活,用你们的生活掠夺生活”、“具有单一才能的人一旦脱离了社会链条,就会毫无例外地变得软弱无力,无论身上的才能有多么突出,此人也将从此黯淡无光。但是把自己的才能融进社会链条,就要接受一些必需的改造,把人身上一些和链条不兼容的成分剔除。于是对于个体而言,情形就仿如一个悖论”。其代表作《我在北京送快递》受到舆论热议,显然也是这种悖论所引发的,看似是与现实和解,但实际则是呈现一种日常困惑下的“自洽”路径。
“自洽”不是为现实扣上精英式的解释——胡安焉显然并不想刻意讨好一切,亦如他成名后对于社交饭局等人情社会的反感或疲惫,以及对于各种身份限定词的警惕。这些年来,胡安焉努力用观察、阅读、思考与笔触界定着自己的节奏,也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以一种相对积极的“自洽”确立自我、呈现自我。
或许,当沉默的胡安焉们开始口述,便是《生活在低处》带给我的最大触动与共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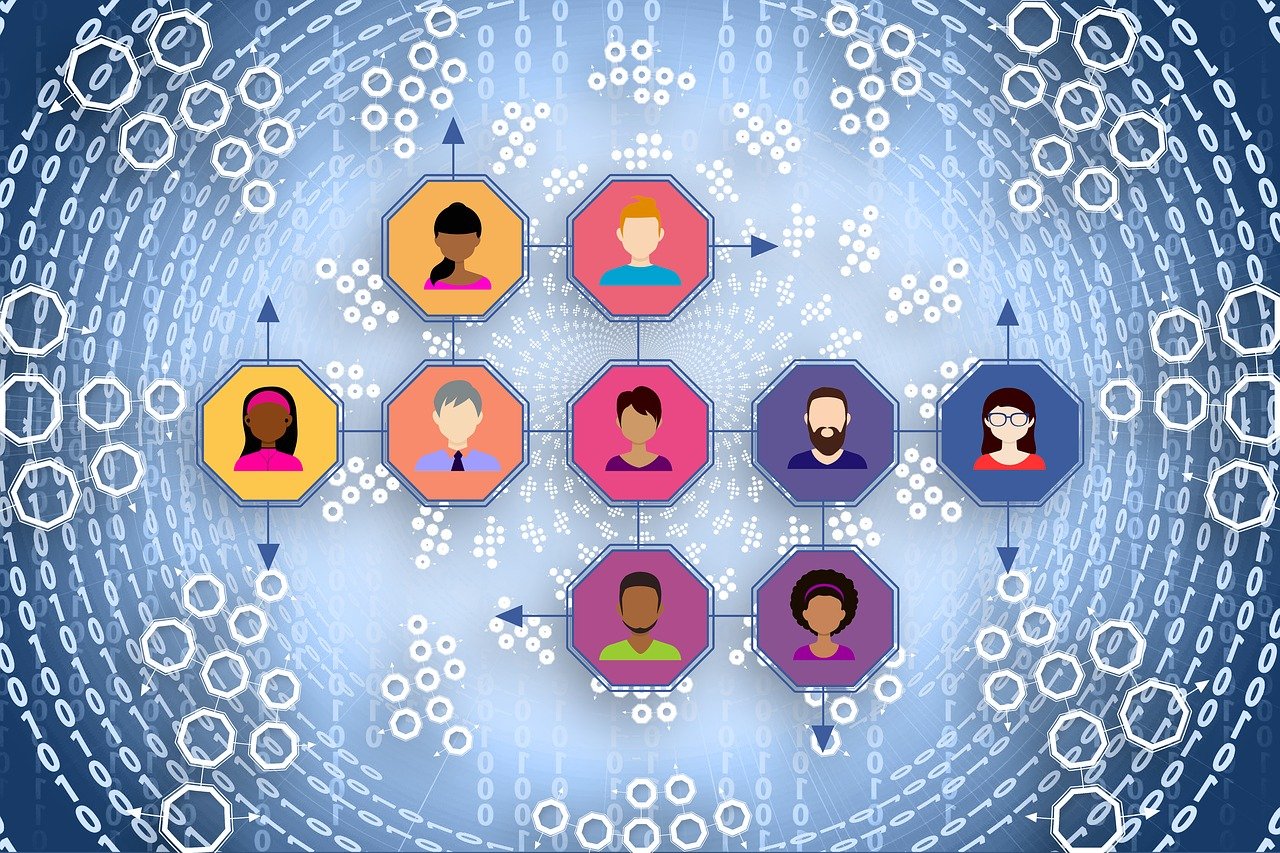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