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觉中国 资料图
逛超市或者菜市场时,我最爱去卖鱼的摊位。如今的市场鱼类品种繁多,但我总是很固执地一眼锁定草鱼或者青鱼,并当场迅速燃起抡勺的瘾来。
草鱼和青鱼是我们当地最常见的两种鱼类,比之其他鱼,犹如田园犬和其他犬,不洋气,但敦实可靠。鲫鱼、鲢鱼虽然也是平常鱼种,但要用在庄严隆重场合,就沦为杂鱼,有点上不了台面。草鱼和青鱼则不同,入得厨房,出得厅堂。
鱼以大为佳,但又不能太大。有些水库或者野塘里,草鱼或青鱼一不留神长到十几二十斤,肉质就开始往粗野的方向发展。虽然作为鱼获能令钓鱼佬们吹几年,但真正吃起来总差点意思。最好是七八斤的鱼,个头喜人,肉质尚嫩,各个部位分而食之,恰好能分三顿。
第一顿,是最适合趁新鲜吃的鱼杂。鱼头下留大约一两寸厚的肉,与清洗干净的鱼肠、鱼子、鱼鳔、鱼尾,宽油煎黄,加热水大火滚两滚,汤汁就是琼脂般的白色。熬够半个钟,加青红辣椒、葱姜、豆豉,已经相当鲜美。也可酌情加豆腐等配菜,不过还是原味最佳。
家常做法的点睛之笔是加新鲜的紫苏叶,独特的植物清香和截然不同的鱼味对撞,意外融合出有层次的风味。这一顿里,有肉有汤,也有筋筋骨骨的头尾,还有不同口感的内脏,堪称合家欢畅享套餐。
在上海很多年,我慕名去吃过不少声名在外的湘菜馆,号称头牌的鱼杂锅里几乎都只有鱼子和鱼鳔,又或者将口味烹制得只剩下一通横行霸道的辣,都很单调;而且很多家都不加紫苏,种种拉胯,连及格分都达不到。
第二顿需要点时间等待。鱼身不刮鱼鳞,以脊骨为界,片成两份。不带脊骨的那份,均匀抹上薄盐,略撒一点白酒,放几颗花椒,常温下腌制一晚。次日鱼肉仍然保留了鲜甜,但略增风味,此时很适合整块红烧,热油煎到有鳞的那面金黄焦脆。另一面煎熟即可,依然热水滚熟,加佐料收汁。鱼肉鲜而紧实,正反面各有口感,拿来待客也很有本土特色。
第三顿则多少带点私人恶趣味。有鳞片的那面打上花刀,仍然腌好,丢进阴凉处的瓦缸里。等到鱼块被腌渍到微微散发出臭味,就成了。此时无论是依照第二顿的做法香煎,还是加上剁椒豆豉焖蒸,都是风味独特的下饭好菜。
鱼肉被腌得紧实Q弹,蛋白质分解释放出的氨基酸等,让鱼肉鲜味大增,尤其是靠近脊骨位置的肉,均衡度最佳。它不像安徽臭鳜鱼那样侵略性十足,又性格分明,是很多人家的私房好菜。
也有人口味比较重,腌鱼时故意少放盐,让鱼肉厚的部位随着发酵微微腐败,鱼肉便呈现出一种臭腐乳般的软嫩,又是另一种风味。这一顿通常不轻易示人,除非是臭味相投的同好。
一条鱼的三顿操作里,多少折射出内外有别,或者进餐者之间的交情深浅。新鲜、方正的鱼肉被称为“正路”,是礼貌端方的一面;非正路们,则是亲切得多的口腹之欲。这样一番料理,一条草鱼或青鱼,几乎被赋予了它作为食材的崇高使命。
外卖缺乏这种使命感,因此常令人有种被浮皮潦草对待的感觉,常吃外卖很容易丧失对生活的热情。但在外面生活久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节奏早已改变,即便真的从市场买条鱼回家做,也以快手菜为主,根本懒得整出这么多花头。
绝大多数时候,我在鱼摊前驻足良久,最后总是空手而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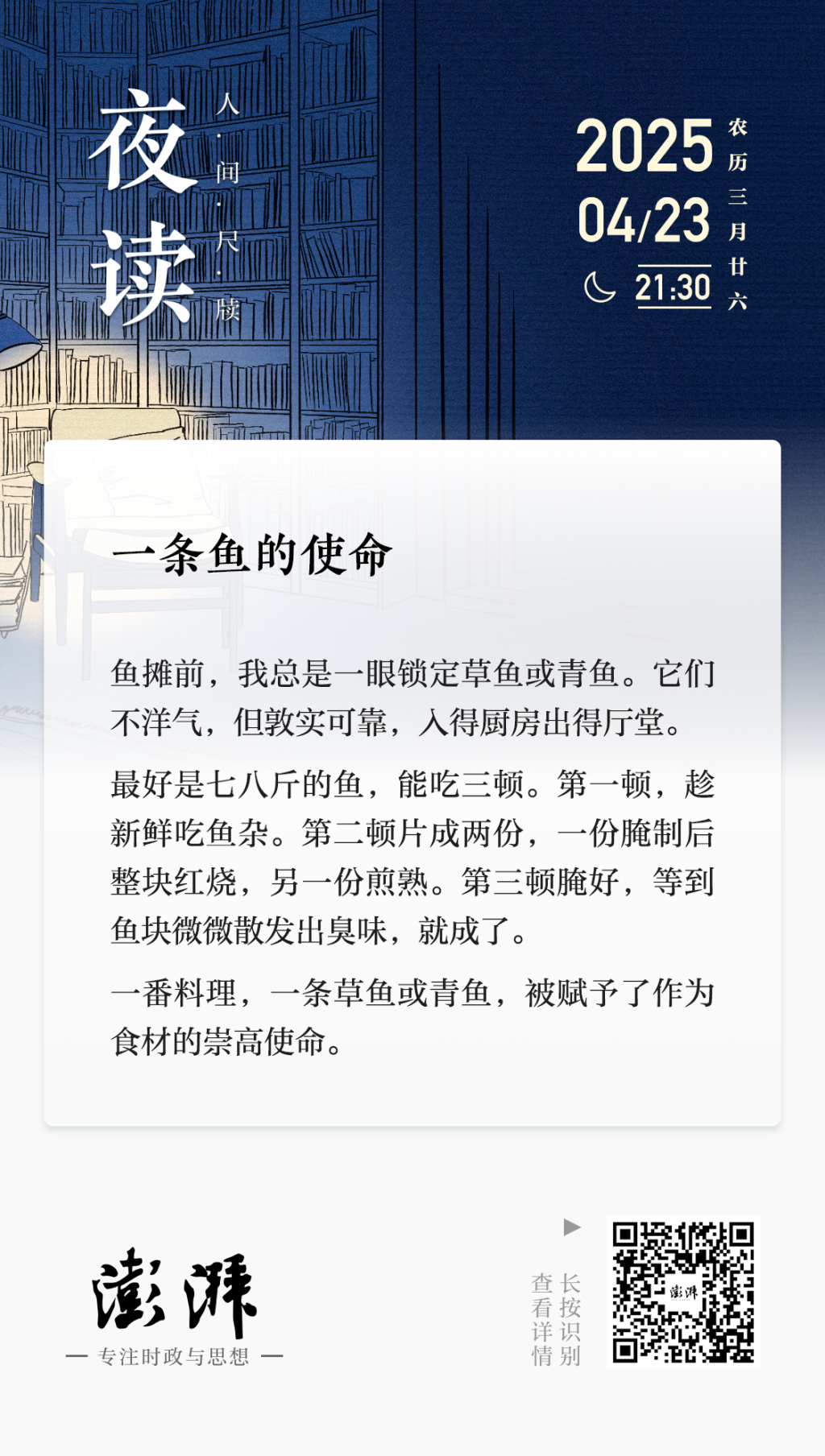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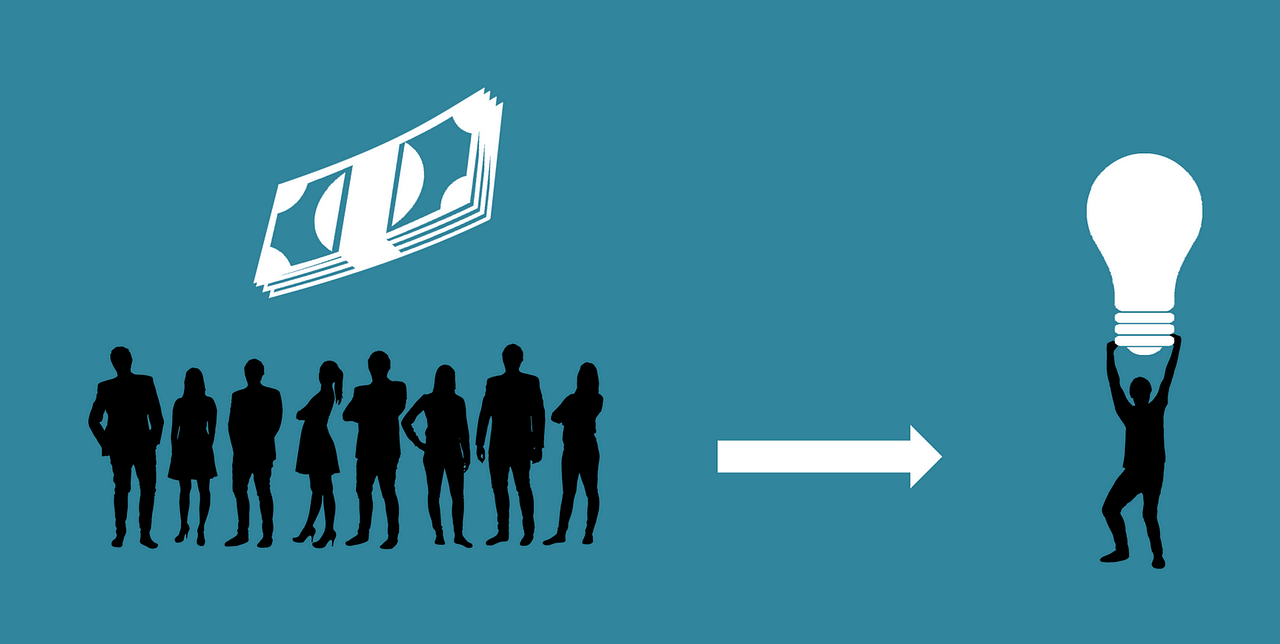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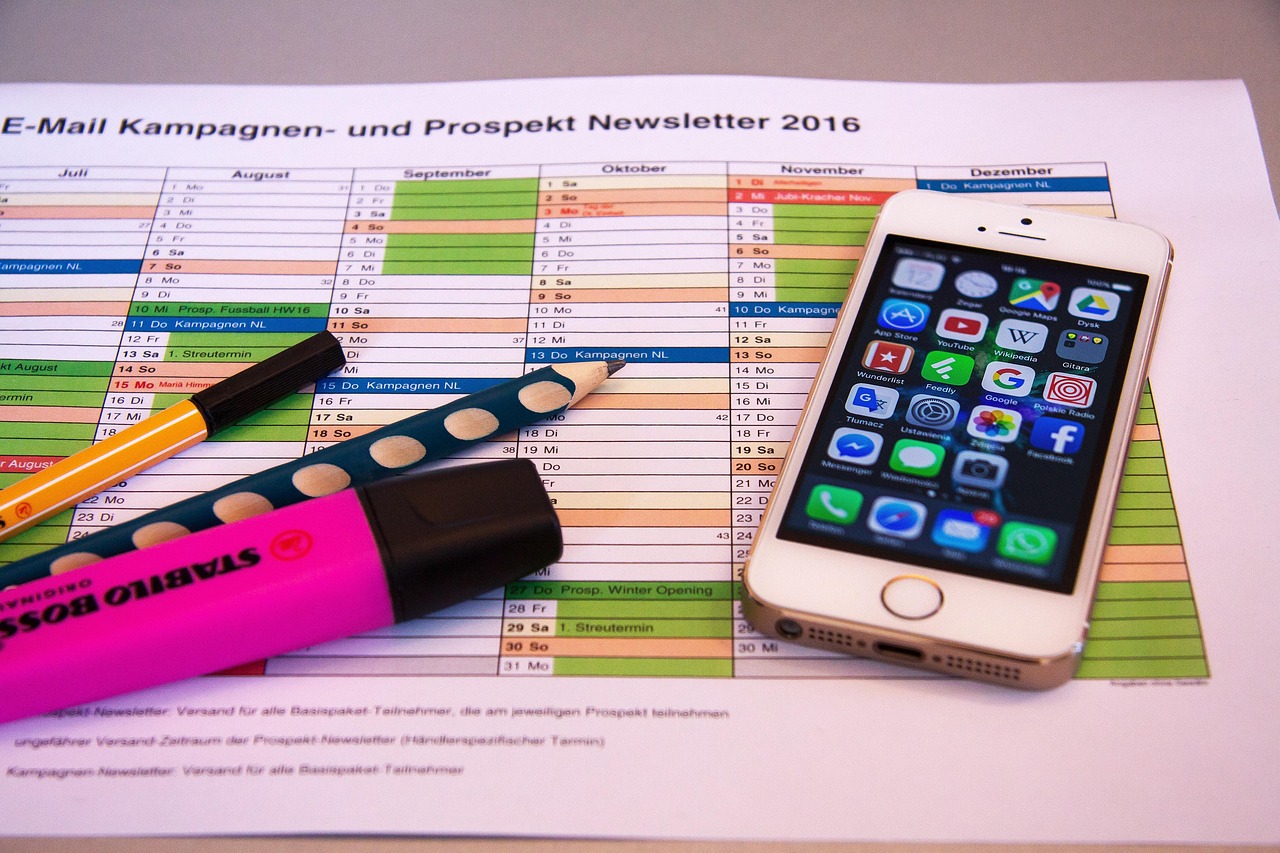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