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懒 27 岁
症状:不喜欢亏欠人情
我的家庭情况比较复杂。弟弟的母亲是我的后妈妈,他在广东出生,爸爸打工的地方。弟弟一岁多的时候,爸爸再次离婚,之后就把他送回了老家。我和弟弟算是奶奶带大的,留守加单亲的状态。
我们住在广西的山村里,两广地区家族联系比较紧密,在老家房子都是连在一起的。叔叔、姑姑家都很近。作为长女,小时候我不仅要看着弟弟,也要一起看着亲戚家小孩。弟妹那时候年纪小,都比较爱闹,吵着要去找爸爸妈妈,不爱吃饭,我就得一直喂,直到每个人吃饱。
大人们工作比较忙,奶奶也要经常去菜地,家里许多事情需要我来做,即使我也还是个孩子。小时候我不理解为什么我得承受这些,也闹过,但没什么话语权,他们要么拿出家长的威严,要么就是要我听话,希望我能给弟妹做榜样。
弟弟没来之前,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挺自由自在的小孩,虽然家庭条件没人家好,但奶奶还是关心我的。后来这份偏爱也被分走了。每次我们俩有矛盾,奶奶都会让我让着他,说我弟以后也是我的 " 娘家人 ",让我对他好一点。
我对弟弟既爱又恨,他是我除了奶奶之外,最亲近的人,但彼此靠近了又会很受伤害。他青春期很叛逆,害我三天两头被老师叫去学校说一通。家里也默认管教他是我的责任,出了事情要我解决,弟弟的电话也只会打给我。
我有时候会羡慕他。那些责任和压力不会落在他身上,他想要什么,就直接说,从来没有愧疚感。我很少主动向家里人提要求,不想让他们为难。
中学的时候,我到县城读,寄宿,每周最难堪的时刻就是伸手跟奶奶要住校钱,那也是她的退休金。奶奶会告诉我,这个钱不是你爸爸给你的,是我出的,以后要还给我。
我很害怕周日。长大后才意识到那种恐惧的背后是卑微:觉得我活在这个世界上,一生下来就是欠债的,父母原本要承担的责任都成了我要负担的恩情,这跟我自己养自己长大有什么区别呢?
高中毕业后,我就没再念书了,想早点独立出来赚钱,内心的负担也能少一点。我在县城的影楼做摄影助理,后来去了市里。从十几岁起,我一直在外面,自己管自己。在外面我基本不怎么和家里联系,也不知道打电话该打给谁。
和同龄人比起来,我心理上要沧桑很多。我没办法像朋友们一样毫无负担地玩。我的主旋律是为自己攒钱,为自己铺后路。我总是走一步想四步,思虑过重。没有人为我兜底,我也承担不起走错路的风险。
我需要安全感,做事蛮畏缩。有时候工作中有调去外面学习的机会,我也不愿意,不喜欢变动,只想做安全型选择。
过早地承担家庭责任,成为大人,对我的影响是很深的。我在外面把钱看得比较重,我自己的钱会紧紧攥在手里。和人家会分得很清楚,吃饭 AA。我讨厌模糊,喜欢互不相欠的感觉,这样都没有负担。我也很不喜欢麻烦人家。
在亲密关系里也差不多。我心思重,没办法很放松地享受恋爱的过程,比较在意结果,但同时又恐惧婚姻。我没有信心经营好一个家庭。做小孩好辛苦,万一我没有办法托举我的小孩怎么办?我辛苦又心酸地长大了,不想他们也经受这些。
刚工作那几年我几乎存不下钱,频繁给家里寄了一段时间钱,工资大部分拿去孝顺奶奶了,给她买吃的,买金首饰,经常给她钱。奶奶这两年身体不太好,住院就起码有六、七次,每次都是我去陪床照顾。大家好像把这当成了我的责任,
剩下的钱我会补偿自己,那时候刚能挣到钱,会疯狂给自己买想要的东西。短短时间内,衣橱就塞不下了,想要的东西一定要去买,完全无法克制自己的消费欲。我觉得那些东西好像才是我的安全感,才是证明我存在过的东西。过了两三年后,慢慢觉得,好像拥有了也就那样。
我现在的愿望是能拥有自己的房子。即使这两年房价在贬值,但之后如果有喜欢的我可能会去贷款买一个。
● 2017 年,15 岁的四川女孩小笒渴望回到学校,但父母要去新疆打工,照顾 8 岁弟弟的任务只能落在她身上。IC photo
小清 23 岁
症状:付出型人格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照顾身边的人成了我的一种习惯。如果在一个集体中,我会优先考虑别人的感受,好像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的性格,没有那么看重自己的需求。
据我观察下来,自己爱负责任的性格和作为长女是有关系的。
在我家,尤其是弟弟青春期后,我经常被当成一个传达信息的中间人,或者家人关系的协调者。我弟在外面闯祸,会找我帮忙而不是爸妈。之前他把同学眼镜不小心碰碎了,要赔钱。他不敢找我妈,只能找我,说先借我的,到现在还欠着我。他最近快要高考,怕自己考不好,压力很大,也会跟我讲。
弟弟读初中时,我在高中,从那时候他的家长会基本都是我去开的。我弟不爱学习,是上课睡觉的那种学生,经常被老师告状。我妈觉得丢脸,不乐意去(学校),就会让我去开会。在家里他很叛逆,谁的话都不听,只有我说话他还听两句。
在我们家,父母对待两个小孩还是挺平等的,但有时一些瞬间会让我感觉到,我妈还是偏心我弟的。我读大学除了第一次去学校是妈妈送我以外,都是一个人扛行李箱,坐高铁,独自往返的。我弟现在高三,马上要准备去读大学,那天妈妈说,如果弟弟以后去读大学,就在他学校旁边租个房子。
还有那次家里要在村里建房子,他们问我自己的房间想要什么样的,我说想要在房间里加安一间厕所,女孩子长大会方便一点。但后来其实也没实现,我分到的房间蛮小。我有跟爸妈讲过,为什么不分我一间大的?他们给我的理由是,弟弟以后要娶老婆的。
和很多更传统的家长相比,他们比较开明,也不会让做姐姐的必须帮衬家里,或者想要拿我的彩礼去给弟弟当老婆本。所以我跟弟弟的关系还不错,他很依赖我。我记得小时候爸妈如果吵架吵得很凶,我就会把弟弟带出去,有一回我拉着我弟问,如果他们离婚了,你跟谁?弟弟说,你跟谁我就跟谁。那个时候他年纪小小的,我很感动。
长大后,我们能够互相感同身受对方的处境。他也会点醒我一些事情,比如之前我大三那段时间,和室友一起学习,我准备考公,她准备考研,比我要努力很多,我就开始焦虑。那天去接我弟放学的时候,和他说了这件事,我弟说,你俩都不是一个赛道的,为什么会在这里焦虑?
我不算成长在很不公平的家庭,但后来我才意识到,自己身上有很多作为长女留下的影子。大学我有两个室友是独生女,她们从小到大没有过住宿舍的经验,刚来学校,我很热情,会主动帮她们铺床,像一个家长一样去照顾她们,虽然我们都是同龄人。
如果我们宿舍一起去爬山,我就是那个爱操心的人,我要看看明天天气怎么样,大家适合穿什么,几点出发,怎么出行,都会当成自己的责任。甚至在亲密关系中,我也是这样。如果对方半夜三更不睡觉,我可能就会说早点睡,不然容易秃头之类的,会嘴碎,有的人会觉得我在管教他。
在朋友们眼里,我是他们遇到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的时候,可以询问的那个人。我会提出建议,也能提供情绪价值,他们会觉得我很贴心。之前有天下午我很忙,手机没怎么看,等忙完发现收到好多条消息,是不同的人来找我。
我以前也想过这种付出型人格是不是有点不值得?但必须诚实地说,我能从家人朋友需要我这件事上获得快乐。我觉得没有必要改变自己为人处事的方式,开心的感觉是真实的。不管我弟弟、我爸妈有些时候带着情绪来找我也好,还是朋友来找我,我会觉得这说明他们把我当成很重要的人。说得难听点,我好像还挺适合当 " 垃圾桶 " 的。
付出型人格也同样让我更懂得人情世故,我从小就比较独立,印象里没有特别依赖别人的时候。有时候会委屈,觉得怎么好像自己一个人在完成许多选择。但换个角度,这也同时意味着自由。每次我跟爸妈提出想法,他们也不会拦着我,让我自己拿主意,决定自己的人生。
●艺人 Melody 和母亲的对谈 图源网络
狸花 25 岁
症状:强调自己的实用价值
二弟弟到 6 岁还不会说话,去医院做检查发现是自闭症。从那之后,我变成了两个弟弟真正意义上的 " 长姐如母 "。
爸妈更忙了,基本上早出晚归,中午不回家,他们需要挣钱,我理解。当时我还在上小学,大部分时间还是我回家做饭。我是走读生,中午可以回家,简单炒个菜蒸个米饭。如果是假期,我就能一直呆在家里。照顾二弟弟是个很精细的活儿,穿衣服、做饭、哄吃饭、哄着他看动画片,他随时会弄脏沙发、桌子、地板、墙面,都需要收拾。
我记得二年级暑假,我趁妈妈在家,出门买了一个冰淇凌。他们都在睡觉,二弟弟就出去了,我跑了一下午,一直喊,一直找,怕得要死,妈妈也是。找到弟弟后,(妈妈)逮着我骂了一通,用柳条往身上甩,现在脸上还有一块疤呢,我也一直以为是我的错,自责了好多年,也就害怕出门了。
我的父母都是他们家庭里最小的孩子,他们是被照顾着的,不理解我的立场。我似乎是他们最合适的 " 树洞 ",他们总对我哭穷,跟我诉说 " 咱家和别人家不一样 "" 赚钱不容易,花钱倒是挺快 "。这导致我花钱总是小心翼翼,没有太多安全感,也会强调自己的实用价值,做一个标准意义上的 " 姐姐 "。
长女这个话题,似乎没办法轻松,更多是对精神能量上的消耗。所以即使我在学校被霸凌,我也还是喜欢学校的,家里实在让我喘不过气。当然,也有温馨的时刻,妈妈会跟姥姥学怎么给我们做鞋,爸爸会给我们买零食,偷偷给我们零花钱。我不能说他们对我很坏,但很奇怪,我在家里一直没有安全感。
到了中学,我坚持住校,妈妈开始放下工作,照顾二弟弟。大学时候,当我撤离这个家庭,我自己养自己一遍。小时候不怎么能出去,长大以后就出去爬山看海,去看苏州的园林,北京的四合院,买很多书,吃自己喜欢的(餐厅)。
我开始学着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 凭什么 "" 我想要什么 "" 我要去做 " 这种念头不断推着我继续我的生活。大学是一种蜕变,虽然很累,但是自由的。我去看心理方面的书籍,进行自我调节。也会在外界,网络上倾诉、提问,看别人的经历,从中汲取能量。
我对他们(父母)的感情从复杂到平淡,更像是合作伙伴。非必要不打电话,我也不喜欢打电话。爸妈对我没那么坏,他们会给我生活费,学费我有助学贷款。毕业后我就直接工作了,收入够我生活和旅游。
后来,我也和其他长女交流彼此的困境。我印象最深的是几个未成年女孩子的 " 求助 ",相比起成年女性,她们资源匮乏,心理也相对稚嫩,也更迷茫。我只能尽量引导她们关注自身,自己的感受,不要被道德感束缚。
如果能回到童年,我希望爸妈把我当成一个真正的孩子看待,清楚知道我未成熟,就足够了,给我健康成长的空间。孩子只是一个孩子。
长女这个问题讨论的人很少,因为总是潜移默化的,一个个实例只是痛苦的微小缩写,很多东西其实并不知道怎么表达,说出来倒是略显矫情,这也是长女话题的其中一项问题。但我也很开心,看到女性(意识)在成长,在社交平台上,谈论起相关话题,评论区变得更和谐,女孩子之间的鼓励不会被 " 攻击 " 了。女性的声音开始被更多地听到。
●湖南某镇中学八年级学生杨文波(后排一),从小分担家庭责任,双休日回家洗全家的衣服,去菜地挖土、拔萝卜。IC photo
千千 脱口秀演员
一位 52 岁长女的女儿
我妈妈是 1973 年出生的,70 后,有一个亲妹妹,一个亲弟弟,是家里的长女。舅舅是年龄最小的,和妈妈相差十几岁,也和我相差十几岁。
按照我妈妈的讲法,她应该上到初二的时候就被要求辍学了,当时,我姥姥要求她必须要回家帮忙干活,经济条件不好,农活之外,还有家里养猪养鸭之类的,劳动量挺大。我外公在重工业厂打工,回家的次数少,主要靠我外婆一个人,比较辛苦。相当于外婆承担了整个家务和养孩子的责任。
我能感觉到妈妈对辍学这件事还是很遗憾的,按照妈妈的说法,退学之前,她的成绩还不错。她自己是一个很爱看书的人。我小时候家里有很多琼瑶的书,一整套的,现在看起来包装会有点做旧复古风的,还有一些已经停刊了的杂志。妈妈年轻的时候,20 多岁,还在当时杂志上发表过一些文章。后来家里书柜为了清位置,大部分都被当成废纸变卖掉了。
大概每一代人都会进步,姥姥不让妈妈上学了,但妈妈很支持我念书,不管是订杂志、报纸还是什么课外书之类,她都乐意,可能也在借此弥补(自己)小时候的缺憾。幸运的是,我小姨和舅舅都是念完了大专的。
而妈妈干农活到 18 岁,就跟着我爷爷去厂里上班了,一辈子都在做工人,我家在甘肃河西铺镇,是个工业镇,主要由铁厂、水泥厂这种重工业厂干下来的。1998 年,她跟我爸结婚,我爸是另一个厂的工人,电工,也比较喜欢写诗,以前家里还有他的书稿。
没有读完书肯定会影响妈妈在工厂的发展。当时那些读到大专的人,妈妈的同龄人们,他们的职业空间肯定更大一些。
作为长女,妈妈小时候可能会觉得委屈,但被那种 " 长女的责任 " 禁锢住,或者说习惯了。她会觉得许多事是她应该做的。我舅舅以前成绩不太好,经常去网吧,然后我妈就把我放在家里,等我睡着以后,再满大街去找他,有那种 " 长姐如母 " 的感觉。
妈妈什么都得操心。我小姨舅舅他们现在都已经成家有孩子了,但妈妈还是会关心,不管是平时打电话,还是逢年过节,她都要发个红包打个视频,看看他们的小孩最近怎么样,有没有长大。是一种习惯性的责任感。她已经内化了这种观念,不像年轻人有那么强的批判性。家庭的连接感对他们很重要,他们还是很紧密的一家人。
我能察觉到小姨对妈妈的依赖。那会儿她刚结婚,孩子还比较小的时候,有回和姨夫闹矛盾,就哭着带孩子回到了我们家找我妈妈。
外婆有些重男轻女,我长大一些才知道,她之前想让我妈再生一个儿子。但我妈还是只要了我一个。
我觉得每一代女性都往前走了一点。我妈妈没有硬把我塑造成什么样子的决心,算是放养式教育。这几年,她的观念也在逐渐转变。我小时候,她会穿很高的高跟鞋,那会儿她跟我说,觉得女人就是要化妆、穿高跟鞋、穿裙子,女人就是要结婚生子,履行母职。但时间长了,她自己也上网,慢慢接受新的可能。有次她讲,一个同事生不出孩子,一直没孩子,现在下班不用着急回家,去跳舞,她也很羡慕。
我妈现阶段的观点是,女孩子结不结婚生不生孩子不重要,但一定要有一个写自己名字的房子。对我这个独生女的期待是,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比如做公务员,有稳定的生活。我姥姥是特别符合社会标准的,始终觉得你要在什么年龄做什么事。以前我的形象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但上大学以后,我回家,她就说你怎么还没有男朋友,你现在不挑好的就被别人挑走了。
但我既不想结婚,也不想生小孩,也不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我是 00 年的,2021 年从南京一所大学毕业,工作了两年多,做过专利事务所写申请书的文员,去过手帐文创店做后台数据,也进过广播电台当导播。24 年 2 月,我搬到云南,开始全职做脱口秀演员。这显然是一份收入不太稳定的工作,但勉强够我生活。
我的理想是全国到处旅居,云南可能算是第一站。和妈妈的感受不同,我不觉得变动的生活意味着漂泊。
我妈催我考公、找五险一金工作的时候,我就会反向催促她。我说你看《秋园》的作者杨本芬奶奶七八十才开始写书,你现在写还来得及,你现在写我还有机会成为富二代。她催我我就去催她,魔法打败魔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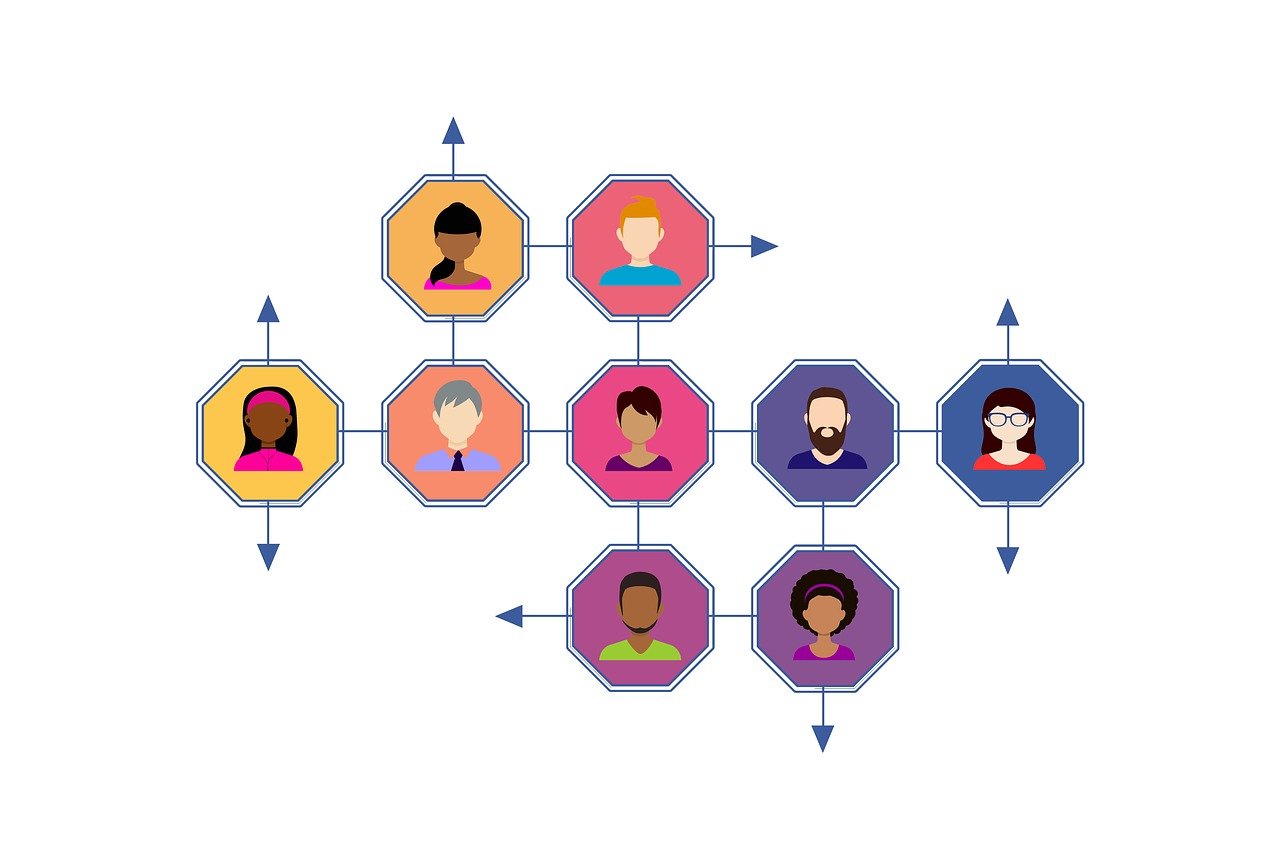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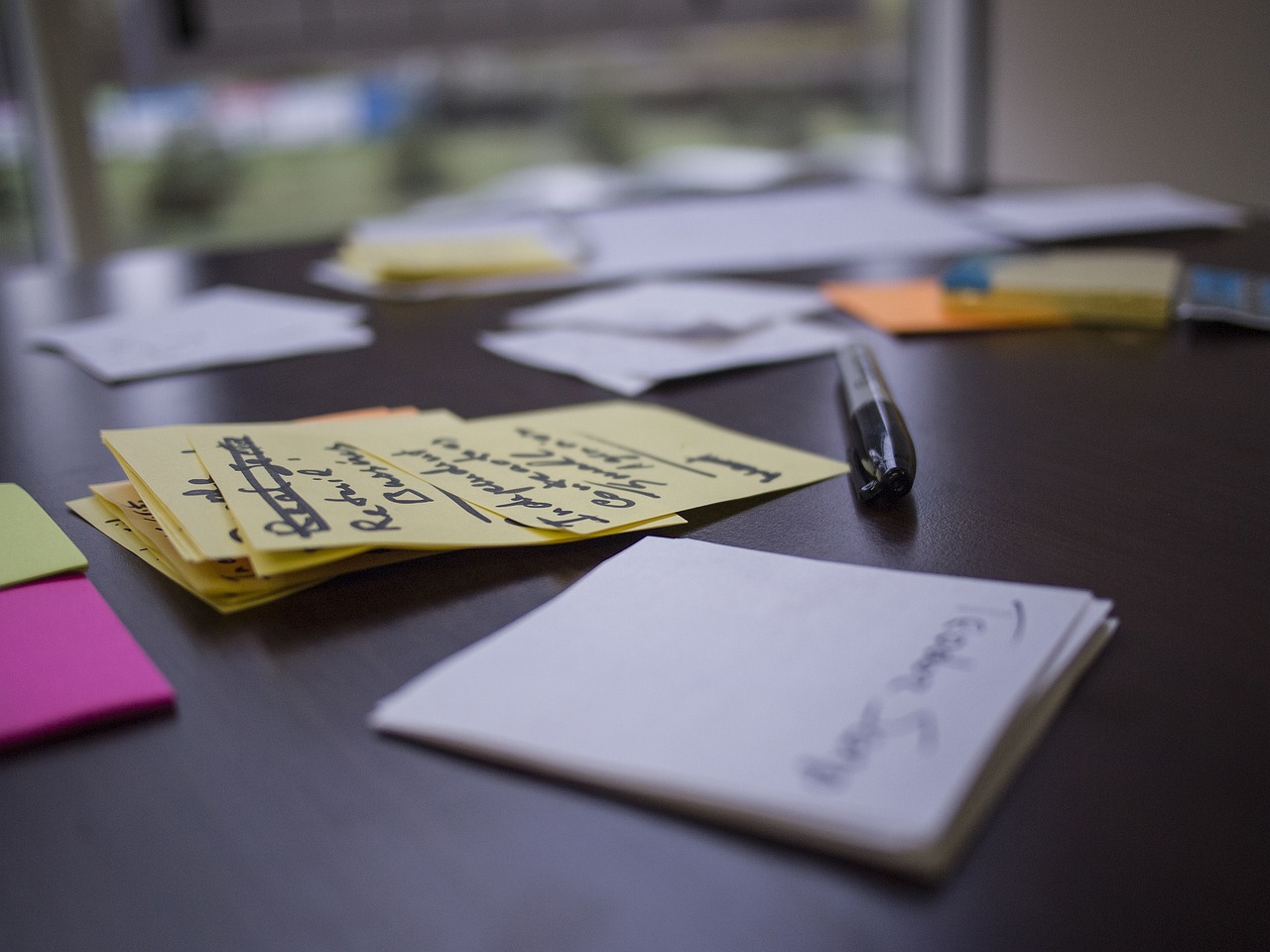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