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舆论》是美国政治评论家、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的代表作,自1922年问世以来,不断重印,成为了“现代新闻业的奠基之作”。近日,该书推出了全新的中文译本。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王亦高为新版所作的推荐序,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

话锋一转,李普曼的深层论证逻辑涌现出来:这并不仅仅是关乎媒介高下的问题,更是关乎人的高下的问题。一般人做不出电影来,那就必须依靠专家:“我们每个人对公共事务的了解都很少,因此,对我们来说,这些事务就会变得乏味且没有吸引力,除非有人用艺术天赋将它们转化成感人的画面。”
在对于人的评价上,李普曼的精英主义思想表现得更趋直白。众所周知,柏拉图的代表作《理想国》曾把芸芸众生分为三六九等,有人生来贵为黄金白银,有人生来贱似废铜烂铁。于是,正如柏拉图只肯选择信赖“哲学王”一样,李普曼也只肯选择信赖专家。甚至,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与专家的科学决策相比,公众认为“合适的”那些决策必是等而下之、形同虚设了。李普曼动辄叹惋公众的“无能”,公众说到底不过仿若“孩童”般幼稚而青涩:
我们在幼年阶段依赖长者进行交流的时代尚未过去,在某些方面,我们要想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仍需通过一些亲近而有权威的人物来完成。他们是我们通往未知世界的第一座桥梁。尽管我们可能会逐渐掌握那庞大环境的许多方面,但仍存在更广阔未知的领域,需倚靠权威才能与之接触。尤其是在对事实所知甚少的情况下,真假很难分辨,一份真实的报告和一个貌似合理的错误读起来、听起来、感觉起来都是一样的。
由此,学界普遍认为李普曼的舆论观彻底颠覆了卢梭的舆论观。在卢梭那里被一厢情愿地理想化了的舆论,宛如晴空之上独照天下的健朗骄阳——却被李普曼不期然地涂抹上了挥拂不去、摇曳未定的忧郁荫翳。卢梭的舆论观从此走向衰落。卢梭曾宣称:“国家的体制愈良好,则在公民的精神里,公共的事情也就愈重于私人的事情。”李普曼却偏偏讲:“公共事务与我们每个人都紧密相连,但我们专注于私人事务。我们的时间和注意力是有限的,而且经常会被日常琐事所干扰。”李普曼甚至得出结论说:
在缺乏有效的环境反馈制度和教育理念的情况下,公共生活的现实与以自我为中心的观点截然相反,舆论很难真正说清楚公众的真实需求和利益。
或者干脆讲:
与基于臆想的舆论相比,基于客观报道的舆论比例其实是很小的。
倘若说,李普曼的观点对先贤卢梭的观点是一种激越的颠覆,那么,其对同侪杜威的观点则是一种审慎的争辩。李普曼强调情报工作的重要性,认为关乎舆论的问题肯綮在于是否能够对外界环境进行准确的描摹与再现。但杜威的许多观点与李普曼大相径庭。杜威实际上认为环境再现并无大用,舆论只能在讨论中且尤其是当讨论在社会生活中变得日趋活跃之时方才得以形成。传播学思想史脉络之中故而还有一段有趣公案:拉斯韦尔的思想更贴近谁或承袭谁?拉斯韦尔受李普曼影响很大,这是肯定的;但拉斯韦尔却不大赞成李普曼的消极态度。学者们进而考证说,拉斯韦尔上过杜威的课并与之有过很多接触,所以杜威等进步主义者对拉斯韦尔的影响更大。
二
不消说,李普曼、杜威、拉斯韦尔,甚至更遥远的卢梭——他们都是大思想家、大学者,他们的观点时至今日依然被屡屡提及与重温。然而,这也并非意味着当代读者便只能厚古薄今、泥旧弃新。芸芸众生身处当下时代,就此刻所谈的观察领域而言,“舆论”究竟又呈现出了怎样的新面貌、新气象呢?下面三个具体分析视角或许能够带来一些启发。
第一是关乎身份基础的视角。李普曼观点的核心始终是社群主义身份理论。社群主义身份理论所追求的,是被一切历史经验与文化符码所构成的作为整体的社会文化环境所塑造的性别、阶级、种族、民族,甚至地域特质等确定与稳定的身份。故而,李普曼叹息道:
这些图景往往是父母和老师灌输给他们的,很少能受到他们自身经验的修正。只有少数人有过跨州出差的机会,出国的人就更少了。
然而,社群主义的话语却始终未考虑一种断裂的语境。特别是进入高级互联网时代以来,随着时空逐渐分离,人类个体被抛入多种“历史经验与文化符码”的缝隙中。此种情况之下,旧有的文化语境被打破,而全新的文化经验尚未塑造出明确的身份认同。于人而言,对现实的强烈意识,恰恰是糅合在一种同样强烈的对现实的离异感之中的。就好像人们常常半开玩笑地说,当下的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跟父母说话,一回到家就把自己反锁在自己的小屋子里,一个人待着。父母能给孩子灌输什么呢?谁能说得准?不论是周遭际遇还是心路历程,父母或许还不如孩子“更辽阔”或“更曲折”哩!
社群主义的话语是一种身份的“考古学”。社群的观点是指向历史的:历史终归是连贯的、寻根的、锚定的。可是,高级互联网时代却显明是指向当下的:当下难免是断裂的、枝蔓的、游移的。文化环境之断裂,可以被视作带有“后现代色彩”的复杂语境,个体在其中要面对多种可能的变化,自我身份呈现的方式故而也变动不居。甚至,“人们恐惧过于牢固的身份认同,害怕在必要时难以全身而退”。如果说,建立在社群主义身份理论之上的舆论所探讨的是关于“他是谁”所以“他该如何”的问题,那么基于游移身份之上的舆论则关注“他欲成为谁”所以“他欲如何”的问题。
殊为吊诡的境况反倒是:不稳定的身份并不能有效地防止个体在某一具体问题上执着于某一偏见,因为,在流动的现代性时代,人们仍要面对个体化的命运,却不再有实现自身“再嵌入”责任的能力。无法“再嵌入”的个体化,使得作为共同体基础的“公民”身份已然遭到了侵蚀与瓦解。或者说,个人伦理抉择是你我互不相连的选择——仅是一种个人的心血来潮或意气用事,却并不作用于社会的选择合力。其结果似乎只能是:一方面是私人问题公共化,另一方面却是严肃政治话题与道德实质问题的琐碎化与肤浅化。乍看来,个体因“相似而重要的话题”汇聚一堂;再闻时,彼此因“固执而浅薄的偏见”四散开去。
第二是关乎呈现形态的视角。李普曼奋力写作的那个时代,总的来说,舆论的形态基本还是以纸质媒体为主——甚至就集中于报纸这一媒体。但目前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高级互联网时代已经赋予舆论以多元化、复杂化、精细化的呈现形态。总的来说,这个世界肯定变得越来越复杂——虽然很难说是不是变得更进步了——人也庞杂,事也庞杂,舆论形态亦复如是。譬如,一个微信表情包甚至仅仅一个微信表情,或许就已经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舆论气候。舆论的形态已然如此多元,几乎可谓“舆论万媒”,任何东西大概都可以成为舆论的呈现载体,意见的交流自然变得更加复杂了。那么,对于舆论的相关分析,也就出现了更为迷离而多变的情况。毋宁说,每种新型的舆论形态都从侧面反映了一个时期的公众心态,特别是对青年一代心态和意见倾向的鲜明表露——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之断语此时此刻焕发出了颇具时代感的理论意义。
第三是关乎时间维度的视角。正如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启笔在文艺批评界收获盛赞一般,李普曼《舆论》的启笔在新闻学术界也备受瞩目。身处于1914年的那个小岛之上,“英国邮船每60天才来一次”。下述情况格外尴尬:
岛上的英、法、德三国的居民们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还在像朋友一样和谐相处,然而实际上他们已经是敌人了。
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跨越空间已经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时间从空间的约束中解放了出来。“流动的现代性”社会之中,统治的权威不再依赖于对空间的占据,而以时间的瞬时性为依据。然而,瞬时性就一定更好吗?倒也未必。塔尔德曾有句名言:“公共头脑有三个分支——传统、理性和舆论;在三者之中,舆论是最后形成的,但也是稍后最容易成长的,而且它的成长要以牺牲其他两个分支为代价。”传统,显然需要时间累积,没有累积便无以成传统;然而,舆论却旋灭旋生,它不需要甚至排斥时间累积。——这种排斥时间累积的情况在当代以更快的速度,毋宁说以加速度的形式持续发展与加剧。我们耳熟能详的舆论情况常常是所谓的:热点频出、观点倏陈、迅速爆款、旋即反转。在这样电光石火的瞬间,受众除了被“屡屡震惊”,其实根本没有“徐徐思考”的时间。没有徐徐的思考,自然也就谈不上从容的理性,李普曼所期待的“诉诸理性”难免成了镜花水月式的痴言呓语。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的研究表明,近年来舆论存活周期不断变短,从原来的两周缩短到一周以内。这正是高级互联网时代令人倍觉沮丧的舆论现状。在时间的飞速流逝之中,大多数人并不真的关心“理性”,人们关心的要么是“震惊”以至“震晕”的个人迷幻感,要么是“自信”以至“自负”的个人陶醉感。此时此刻所体现或勃发而出的“舆论”,在极大程度上,不过是流曲百转的社会信息与复杂万殊的关系网络在特定社会事件或相关讨论中的暂时性、偶然性的“结晶化”或“定格化”。舆论,迅速爆发,又迅速湮灭,在完全来不及思考的瞬间里,已被高级互联网时代所推送出的浩瀚信息之潮与汹涌观点之流无情又无奈地冲刷进记忆的渺渺汪洋之深处。
三
前文提及了当代研究的若干新视角,此时此刻,我们却不能不再次回望李普曼的一个重要观点——新闻的“职业”问题。大家都知道,李普曼的“正业”其实是报纸专栏作家。在讲述与讨论了关于舆论的种种困囿与迷茫之后,李普曼对自身的工作领域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李普曼明确说过“新闻学院是职业学院”这样的话,甚至由此推断了某种“职业时代”的来临——新闻业似乎是作为一个纯粹的“职业”而立足于社会的,它不该再是其他什么东西或什么力量(或政府、或党派、或广告商)的派生物。这一判断毋宁说是极具历史眼光的,它对于当代世界的新闻业发展、新闻学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意义。譬如,李普曼坚定地认为“新闻必须是已经发生的一些确凿无疑的事实”,并言简意赅地断定:
整个新闻报道体系就由以下要素组成:纷繁复杂的背景情况、为人所知的标志性的公开行为、在刻板印象下对事件进行报道的报纸以及读者从直接影响自己的经验中提取出的观点。
然而,正如读者立刻便会发现的,李普曼的悲观情绪即使在这些具体问题上依然挥之不去、拂却还来。虽然李普曼悉心肯定并用心勾勒了作为职业的新闻业的独特品质,但他还是倾向于认为新闻业自身的工作方向不免失于盲目,对健全舆论的形成终归助益无多。因而,唯一的解决之道又回到了老路上,即聆听科学专家之言:
我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舆论要健全,就必须由新闻界以外的组织来为新闻界提供组织,而不是像今天这样由新闻界自身来组织。我认为,这种组织工作首先应由政治学家来承担。
在李普曼心中,专家应该是也必须是公正的,他们焉能不公正呢?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谁来裁定公正还是不公正呢?《群氓的时代》曾经譬喻说:“法律是父亲不在场时的一种象征。每当父亲以一位领导人物的身份再次出现时,他便架空法律并将此附在他自己制定的无法无天的规则后面。”如果我们把“父亲”置换为“专家”,其结果如何?
怀着如此忐忑的心情,我们不禁提问:《舆论》究竟是一本怎样的书?《舆论》勇敢地提出了许多针砭时弊的真问题,但给出的答案却显得不够有底气;《舆论》力图廓清与抬举新闻业,又似乎同时对新闻业加以质疑;《舆论》是新闻传播学领域的专业作品,又貌似是一本兼顾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语言学的通识读物;《舆论》所举证与描摹的不少案例与场景在今人看来已然相当有隔膜、陌生、难解其妙,但其文笔却又如此晓畅而通达,竟能把五花八门的素材有条不紊地归拢在一道并以一种鲜明而不失灵动、审慎而不失诙谐的方式呈现出来。
作为译者,夙夜匪懈!文雯的新译使《舆论》这部经典作品再度焕发出熠熠之辉,其翻译工作——无疑为新闻传播学建设添砖加瓦——艰辛而卓绝。
作为读者,开卷有益!面对如此广识、深智之经典,面对如此达意、传神之译笔,我们更应该相信阅读与思考所积蓄与蔓延的力量:持久而至恒长,温柔以臻热烈。愿我们在追寻真理、爱与自由的大道之上,奋勇前行,永不停歇。
王亦高
2024年芒种于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新闻楼
(王亦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传播理论、新闻理论。)

《舆论》,【美】沃尔特·李普曼/著 文雯/译,湖南文艺出版社·好读文化,2025年3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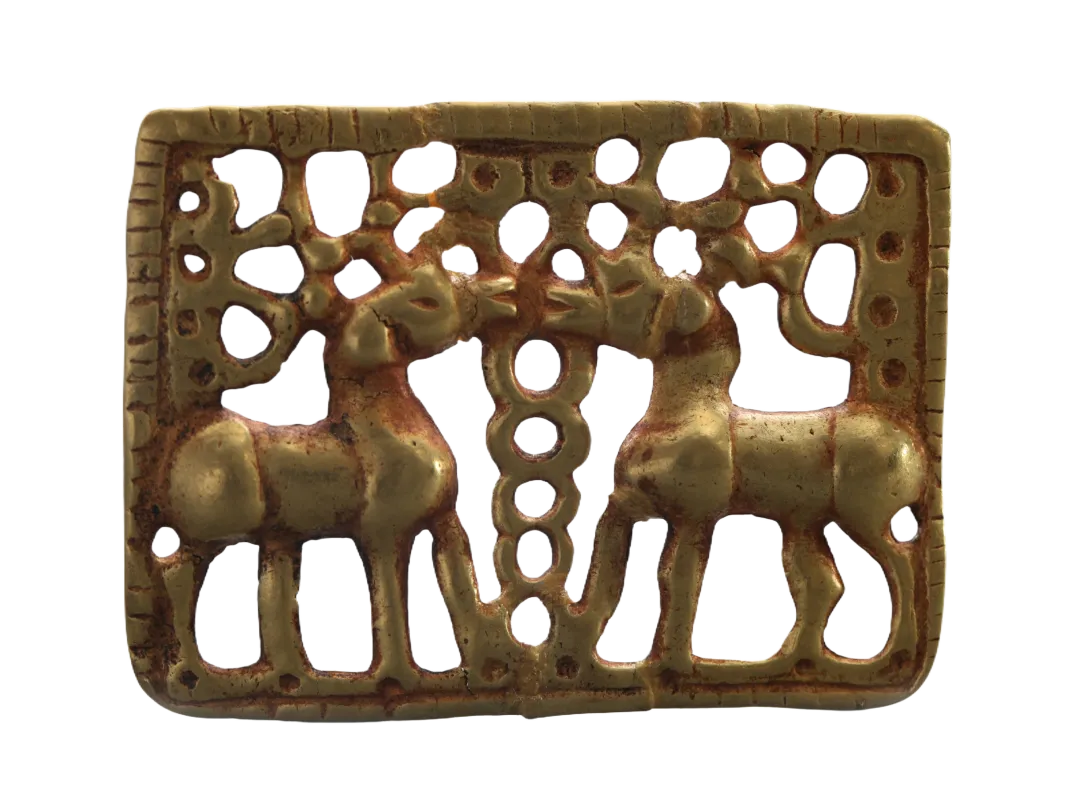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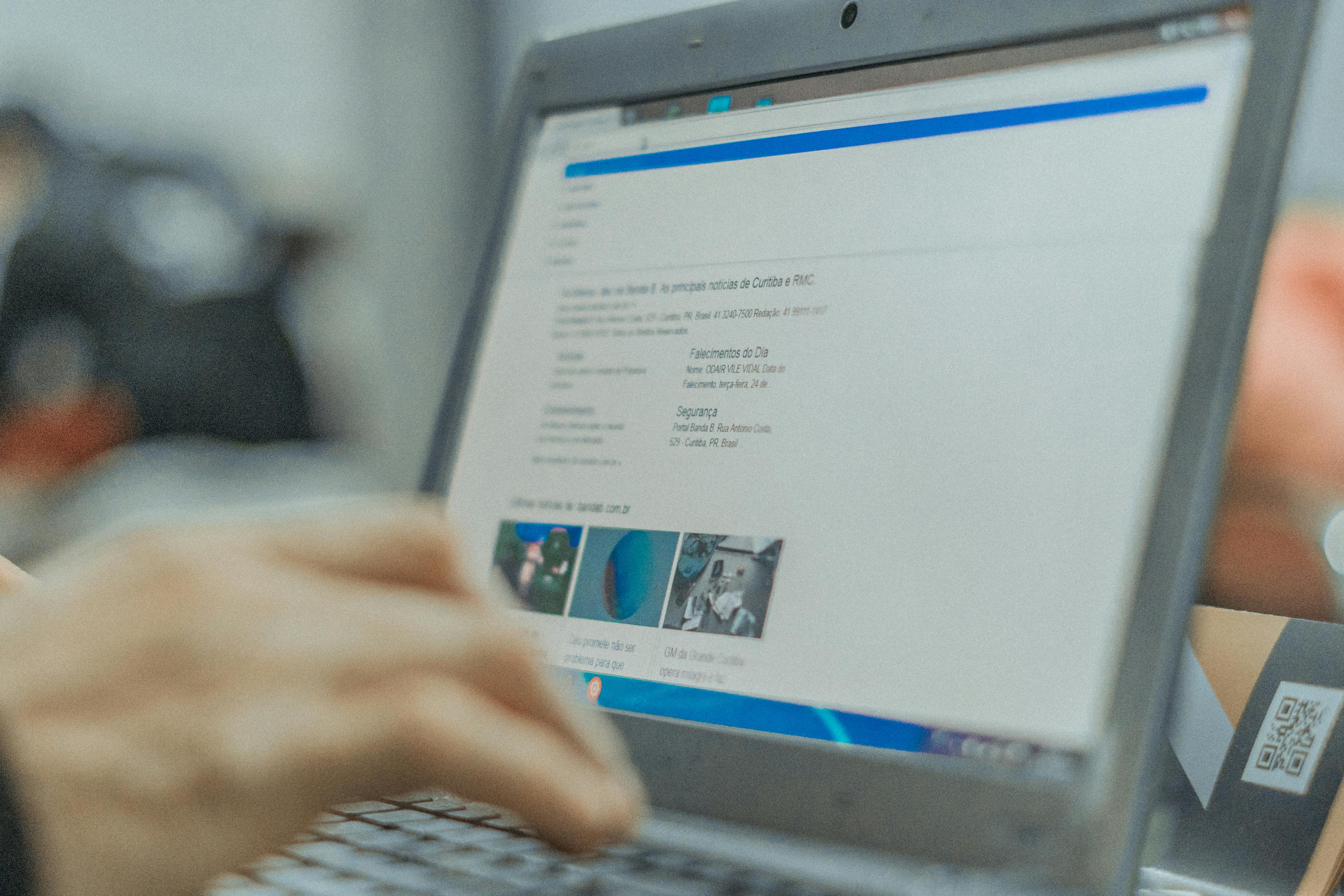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