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德·贝尔伍德(Peter Bellwood),国际知名考古学家,现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考古学和人类学学院教授,曾任该校考古学与人类学学院院长。其主要学术专长是从考古学、语言学和生物学角度研究东南亚和太平洋史前史、全球性的农业起源及其后的文化、语言和生物学的发展。
贝尔伍德教授著作等身,目前已出版专著15部(其中数部专著被译为他国语言)、期刊论文76篇、专业书籍论文74篇;与他人合作论文53篇;受邀评述他人著作60余篇;此外,还参与编辑考古学专著8部、编辑考古学期刊30余种。其中,1978年出版《人类征服太平洋》(Man’s Conquest of the Pacific)、1985年出版《史前时期的印度-马来群岛》(Prehistory of the Indo-Malaysian Archipelago,1997年修订),作为世界许多大学考古系的经典教科书长达二三十年。特别是2005年出版的《最早的农人》(First Farmers)一书获美国考古学会2006年度全球最佳考古学著作、考古学和人类学最佳专业出版著作两项殊荣。目前已陆续被译为不同语言出版。
贝尔伍德教授1943年出生于英国莱彻斯特(Leicester),后就读于英国剑桥大学,1966年获大学学士学位,1969年获硕士学位,1980年获博士学位。1967-1972年任新西兰奥克兰大学(University of Auckland)史前史讲师;1973年至今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先后担任史前史讲师(1973-1975)、资深讲师(1976-1983)、考古学准教授(Reader,1984-1999)、考古学教授(2000-今)。贝尔伍德教授曾先后指导硕士、博士研究生30余人,这些学生分别来自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中国大陆、台湾地区、菲律宾、老挝以及澳大利亚、美国、英国、新西兰等。
贝尔伍德教授曾任印度-太平洋史前史协会(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秘书长及执行编辑近二十年(1990-2009)、新西兰考古学学会会长(1971-1972)及美国《世界史前史期刊》(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编辑等职。现任美国《考古学评论》(Review of Archaeology)、台湾《南岛语族研究期刊》(Journal of Austronesian Studies)编辑及荣誉编辑,美国《亚洲观察》(Asian Perspectives)、《考古学方法和理论期刊》(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顾问,香港《亚洲人类学》(Asian Anthropology)国际顾问、马来西亚“婆罗洲研究理事会”(Borneo Research Council)国际顾问,瑞士日内瓦“巴尔比耶-穆埃勒博物馆”(Barbier-Mueller Museum)之友荣誉会员,日本“京都人文自然研究所评议委员”及“澳大利亚人文学院”(Australian Academy of the Humanities)院士。
本文特邀洪晓纯博士对贝尔伍德教授进行了采访。洪博士师从贝尔伍德教授(博士研究生、博士后研究员),现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执教。她与贝尔伍德教授一起参与了多项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以下为采访内容。

彼德·贝尔伍德教授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您一直是东南亚和太平洋考古最具代表性的考古学家之一。可否请您谈谈您对这个区域的研究兴趣开始于何时?以及您这40年来的研究主题有什么变动?
彼德·贝尔伍德:我对考古学的兴趣始于1960年,那时我才17岁。原因是那时我阅读了一些和考古学相关的大众读物。当时,我在家乡——英国莱彻斯特(Leicester)的一家制鞋工厂作学徒。1963年,经过考试,我获得英国政府的奖学金,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在那儿我学习罗马及欧洲考古直至1966年完成大学学业。
那时,在剑桥大学除了格拉汉姆·克拉克(Grahame Clark)这位经济考古学和欧洲中石器考古学的权威外,我还受教于专长于社会人类学的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教授、欧洲新石器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Glyn Daniel)、经济考古学教授艾瑞克·希格斯(Eric Higgs)、盎格鲁-撒克逊考古学(Anglo-Saxon archaeology)教授布赖恩·霍普-泰勒(Brian Hope-Taylor)及罗马考古学教授琼·利弗西奇(Joan Liversidge)。大学期间,我参加了在突尼斯、利比亚、法国、丹麦、土耳其及伊朗等地的考古工作,并在英国参加了罗马时期及中世纪考古遗址的发掘。
在剑桥的考古训练,让我一直对考古学、历史及人类文化之间的关系保持了长期兴趣。1960年代中期,当我还是大学部学生时,恰逢所谓的新考古学(New Archaeology)冲击到美国和英国考古学界,但我一直对这种不太注重历史进程、却以程式化推论研究人类历史的方法不感兴趣。
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历史”、“演化”及“迁徙”一直是我的研究兴趣之所在。在我就读于大学时,由于阅读了考古学先驱罗伯特·瑟格斯(Robert Suggs)的作品,我对波利尼西亚(Polynesia)考古产生了很大兴趣。20世纪60年代,波利尼西亚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富有浪漫色彩的地方。200多年来,那里的史前人类大迁徙景象一直像谜一样困扰着西方人的想象。
1966年,我申请前往新西兰的奥克兰大学(University of Auckland)担任讲师。紧接着,1967年我从英格兰移民到新西兰。当时我23岁,还没有博士学位。那时,英联邦国家的大学扩展相当快,而且只要你是从牛津或剑桥大学毕业的,就能拿到一个在大学教书的终生职位。这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想象。如果获得博士学位,在工作上肯定会有升迁机会。1980年,我提交了4部我写的新书及专题论文作为我博士论文的替代物,并从剑桥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当时剑桥大学有个特殊规定,允许往届毕业生、像我这样已有全职教学职位、但却难以全力花三年时间投入博士论文写作的人,以这种替代的方式申请博士学位)。
我在奥克兰大学待了6年,那段时间,受同事罗杰·格林(Roger Green)和安德鲁·波利(Andrew Pawley)的影响,我深刻体会到,历史语言学对重建人类过去的重要性。我开始在波利尼西亚和新西兰进行田野考古工作。1967-1970年,我在新西兰进行考古发掘和调查。1967-1968年,我和夏威夷毕晓普博物馆(Bishop Museum)的筱远喜彦(Yosihiko Sinoto)博士一起在马克萨斯群岛(Marquesas Islands)发掘。1968-1972年,我到库克群岛考古。1972年,约翰·马伟宁(John Mulvaney)教授刚刚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建立史前考古学系,我便受邀到这个系做讲师。1973年我移居澳大利亚。此后,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一直工作到现在。如今该系已扩展为考古学与人类学院。
在奥克兰大学期间,我有个远房亲戚叫皮特·勒温(Peter Lewin),当时他在伦敦一家出版社工作。他联系并建议我向国际出版公司申请合约写书。1978年,我的第一部和第二部著作相继问世,此即由奥克兰的科林斯(Collins)和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人类征服太平洋》(Man’s Conquest of the Pacific)及伦敦泰晤士和哈德逊(Thames and Hudson)出版社出版的《波利尼西亚人》(The Polynesians)。
1970-1978年间,我深入思考了包括从考古学、生物人类学及比较语言学的视角观察的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史前史。当时比较语言学并不像考古学和生物人类学那样深入应用于解读南岛语族的历史(如今流行的人类基因研究当时还只处于萌芽期)。也正因为如此,却让我发现了今日在语言族群里所称的南岛语族,是可以凭借考古学证据找到他们遥远祖先的,这中间的联结确实具有重大意义。
随着我对探索南岛语族史前史的兴趣愈来愈大,以及由来已久一直对新石器人群扩散的热衷,1972年,我将波利尼西亚的田野工作转到了东南亚岛屿。此后,我的考古发掘地点涉及东印度尼西亚的塔劳群岛(Talaud Islands)、摩鹿加群岛北部(northern Moluccas)、东马来西亚的沙巴(Sabah)和北婆罗洲(northern Borneo)、菲律宾巴丹(Batanes)群岛等。显然,不论此时还是彼时,尽管波利尼西亚是如此的广阔、岛屿之间距离是那么遥远,但事实上它只能是古代大洋洲航线的一个终点而已。
南岛语族并非在波利尼西亚发展出他们的文化及语言。我们必须到它的西方——即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岛屿追溯其根源。1974年以来,我的大部分田野工作都在东南亚。从1978年至今,我的学生中的大部分来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而且他们都在那些区域做过相当重要的研究工作。2004年以后,我的兴趣转到越南,但研究焦点还是放在新石器时代。
虽然我也做过一些其他的考古工作,包括印度尼西亚旧石器、马来西亚的和平文化(Hoabinhian)、距今2000年前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文化接触、越南北部的青铜文化及东南亚史前时代晚期的陶器贸易等,但我的研究兴趣主轴一直集中在早期食物生产族群的历史及其经济和语言。
目前,我的研究焦点已转向全球性的议题,正如我在2005年出版的《最早的农人》一书中所讨论的、在全球各大洲最早从事粮食生产的族群的扩张,还有我目前正在为美国和英国的威利-布莱克威尔(Wiley-Blackwell)出版社撰写的一本新书,关于全球的人类迁移史。我讨论的范围早到200万年前非洲的人类祖先、晚至800多年前到达波利尼西亚东部的人群。无疑,中国在这两个史前人类迁移的重大事件中均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
在您如此丰富、多地点的考古经历中,有哪些地方是特别值得您回忆的?
彼德·贝尔伍德:我最早的考古经验是我记忆最深刻的。这包括我上大学之前参与的第一次考古发掘。那是1961-1963年在英格兰的赛伦塞斯特(Cirencester)和莱彻斯特,它们都是罗马时期的古城。我在那儿担任志愿者和遗址管理者。1963年,我到意大利的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当志愿者。1964年,我和诺曼·哈蒙德(Norman Hammond)沿北非突尼斯(Tunisia)和利比亚(Libya)的古罗马道路寻找考古遗迹。1966年,我和克莱尔·高夫(Clare Goff)在伊朗西部的卢利斯坦(Luristan)省发掘一座大型的人工土丘(tepe)遗址。1967年,我和筱远喜彦在法属波利尼西亚的马克萨斯群岛发掘岩荫遗址。1967-1968年,我和我的学生开始了在新西兰和库克群岛(CookIslands)的研究计划。
1971年,我开始了在东南亚的工作。通过和印度尼西亚考古学者伊·瑁·舒塔雅莎(IMadeSutayasa)的合作,我完成了在印度尼西亚东北部相当偏僻的塔劳群岛的发掘。接着,1978年,我和沙巴博物馆在婆罗洲北部、沙巴雨林东南部进行了一个合作发掘研究项目。1990年,我和杰弗里·埃尔文(Geoffrey Irwin)、古纳迪·尼提汉密诺托(Gunadi Nitihaminoto)开始在印度尼西亚摩鹿加群岛北部实施一项研究计划。到20世纪90年代晚期,由于这个区域社会动乱日益严重,我们遂将研究转移到菲律宾北部的巴丹群岛。这项研究是2002年我和亚瑟·安德森(Atholl Anderson)、乌沙毕·狄容(Eusebio Dizon)合作的。2004年以后,我开始到越南北部和南部发掘,合作同行包括茱蒂丝·卡梅隆(Judith Cameron)、阮越(Nguyen Viet)、阮金容(Nguyen Kim Dung)、欧·马克(Marc Oxenham)和卜志黄(Bui Chi Hoang)等。
从1961年我还没成为考古系学生之前至今,我已在20多个国家做过考古工作。其中有不少是和我的研究生一起做的调查发掘,基本都是以学生的硕士或博士论文的研究为目的的。我对这些研究的机会总是心存感激,因为在这些不同区域的工作让我看到了世界上的族群是如此多样化,也看到了每个单一的史前文化都有其重要性,而不仅仅是那些醒目的、强势的文化,或那些征服了别人、拥有霸业的古代文明。
对我来说,那是最激动难忘的田野记忆。我永远记得那些挥汗如雨的挖掘、一层层深入的探沟、一次次期待有特殊遗物乍现的心情。那些细细的网筛、沙漠中的干燥高温及飞扬的尘土,抑或热带雨林的闷热潮湿。当然还有那些一起挖掘的民工、研究生、同行以及以前的师长……其中,有些人已远离我们而去。
自然,难忘的记忆也包括不时乍现出土的小件文物:如在英国罗马时代的排水沟内发现的一枚金戒指、在越南北部东山文化遗址出土的一艘榫卯结构的船、在菲律宾巴丹群岛发现的一件来自台湾的玉耳环,甚至在东马来西亚沙巴的骷髅山(Bukit Tengkorak)出土的一件黑曜石——它是3000多年前从美拉尼西亚(Melanesia)的俾斯麦群岛(Bismarck Archipelago)旅行了3000余千米到那里的。通过对这一件件小玩意儿的分析研究,让我们有了更深层的认识。也正因为多年来这些点点滴滴的发现,丰富了我所写的书和文章。
在您的考古研究中,有哪些特别重要的发现?
彼德·贝尔伍德:通过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研究,我发现世界上几个主要语族的扩散和早期农人的迁徙密切相关(如欧洲所称的新石器时代、美洲所称的形成期)。那时,剑桥的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也正就此议题研究印欧语族和欧洲的新石器时代,我则着力于南岛语族和东南亚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工作是各自独立进行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的南岛语族研究经验让我确认,农业发展、人口增加、语言扩散这样的连带关系是唯一能合理解释其发展过程的(阐释)。当然,海洋技术也在南岛语族扩散的进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这种早期农人和特定语族扩散间的连接,不仅可以用来合理解释南岛语族的情形,也适用于世界上其他几个主要的农业语族,但它并不意味着人口的全面取代。我们应将其视为一个渐进过程,包括人口扩张和种群混杂。如同我们在世界许多地方观察到的,中国也是如此。有一些和我持不同理论观点的人长期一再批评我,认为我主张早期农人全面灭绝了狩猎-采集民族。事实上,他们大部分人并未仔细阅读我的论述,所以才会出现这种错误指责。
就考古发现而言,我不能说我曾发现任何古代文化或古物能让我们瞬间革命性地了解人类历史。但我想,有些考古工作开启了许多区域性的新视野。正如我20世纪60年代末在新西兰挖掘一个毛利人(Maori)文化的防御工事遗址时,所获取的重要材料让我们得以了解此类遗址的内部组织和防卫结构。1990年代,我在摩鹿加群岛北部发现一个35000年前的旧石器遗址,它坐落在通往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的古老迁徙通道上。1974年,我在塔劳群岛的发掘让我认识到,在新石器时代,特别是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东部广泛分布红衣陶器(red slipped pottery)的重要文化内涵。2004年,我在越南北部东夏(Dong Xa)遗址发现的一条船让我们认识到,2000年前,东南亚和地中海可能即存在文化接触。前几年我在巴丹群岛的工作找到了重要证据,证明史前时期南岛语族从中国台湾迁移到菲律宾的事实。最近,我们在越南北部的发掘发现了4000年前人们已在那里种植粳稻,推测它们来自中国长江流域。而且当时人们也养猪、狗,并制造陶器。越南的这些发现和近年来在泰国中部、东北部的发现相当接近。
您2005年出版的《最早的农人》一书荣获美国考古学会2006年度最佳考古著作、考古学和人类学界最佳专业出版著作两项大奖。此后,这本书陆续被译成多种文字,已相继出版了日文版和越南文版。您是否能谈谈,您最初是如何产生写这本书的想法的?
彼德·贝尔伍德:在经历了这么多年对南岛语族的研究后,我认为他们的大迁徙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中国华南和中国台湾的族群。因此开始思考史前时期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情况。20世纪80年代,科林·伦福儒正在研究新石器时代早期印欧语族的农人如何从安纳托利亚(Anatolia)进入欧洲。与此同时,卢卡·卡瓦利-斯福札(Luca Cavalli-Sforza)和阿尔伯特·阿门曼(Albert Ammerman)也开始用相同的视角,从考古和遗传学角度审视欧洲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只不过后者没有考虑语言这一要素。
事实上,我们必须将语言学、遗传学和考古学三项要素一并加以考虑。如此,再来看世界其他各大语族1500年前的分布,像南亚语族(Austroasiatic)、亚非语族(Afroasiatic)、班图语族(Bantu)、汉藏语族(Sino-Tibetan)、犹他-阿兹特克语族(Uto-Aztecan)和易洛魁语族(Iroquoian),就可以对相同的现象做出合理解释。当然,并非所有语族都扩张到相当庞大,而且也不是所有扩展到非常庞大的语族都是由早期农业人口膨胀造成的,我并不主张语族形成和农业扩张理论适用于所有个案。但从目前看,这个理论还是可以解释大部分案例的。2003年,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曾邀我就此主题与他合作,为《科学》(Science)杂志写篇文章。2001年,我曾与科林·伦福儒就此议题在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学研究所(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联合组织了一次学术会议。
关于您刚才提到的语族和农业扩张理论,最近有什么更进一步的想法吗?
彼德·贝尔伍德:我的早期研究或许倾向于对世界许多地区的推论。在狩猎-采集经济转变为初期农业后,农业扩张立即快速地发生了。但这几年新的研究显示,一个全面的农业经济,包含生产粮食作物和家养动物、从早期栽培野生植物和驯养野生动物,需要几千年的发展过程。在中东、中国和中美洲所看到的这一过程,至少经历了3000年之久。举例说,在地中海东部的黎凡特(Levant)及安纳托利亚地区,从纳吐夫文化(Natufian)一直到前陶新石器B(PPNB)结束;在中国长江下游则从上山文化一直到崧泽文化。
虽然我们试图对这些最早的“农人”从生计模式给出一个经济属性的定位,但这些最早的农人可能不是着手大规模迁移的人,大规模移民可能稍晚后才出现。大量的人口都必须依靠粮食生产,并且更为集约地对其周围环境给予较大影响时,这些促使他们必须寻找新的资源和新的土地,尤其是在当时那些狩猎-采集民族居住的地区。
我认为,目前考古学、遗传学和比较语言学的研究结果都相当支持这个农业-语族扩张理论(language-farming model),尤其是在那些拥有早期农业、特别核心的地区,如中东、撒哈拉以南非洲北部(northern Sub-Saharan Africa)、中国、中美洲、安第斯山中部(central Andes)及亚马逊流域(Amazonia)。尽管不少人反对农业-语族扩张理论,但这些反对者很少能提出有根据的、严密的观点,他们大多只是自然地表述想要避免在解释人类史前史中特别重要的行为模式时使用像移民(migration)这样的说法。不过,现代人走出非洲是他们允许迁移说的一个例外。
原生狩猎-采集民族与外来农民之间的基因混杂,甚至他们提供了多少特有的文化知识给外来的农人?这些年来,我在这类议题上的看法也有某种程度的松动。我认为,如果没有大量农人进入狩猎-采集民族的领地,很难想像狩猎-采集民族会突然接受农业。我在《最早的农人》一书中所称的“摩擦区”(friction zones)是指外来农业人口并未在狩猎-采集民族领地享受到人口优势,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那些发展农业条件相对较贫瘠的地区,有可能是气候因素,也有可能是其他环境因素。也有另一种可能,即当地原生的、大量狩猎-采集民族的祖先可以在这种区域接受农业,进而他们人口增长,才有了对外扩张。
我认为,语言-农业模型(language-farming model)对新石器扩张最重要的启发是,它解释了人类在大殖民时代(公元1500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的种族分布(racial distributions)。这里我所谓的“种族”(racial)分布是指根据表面特征、纬度和地理区域可做出的区分。现在已没有人认为“种族”是固定的,或有界线的一个实体,它应该被看成是史前及历史阶段、大量人口移动而逐渐形成的一个结果。
但即便如此,种族区分还是清楚地见于像非洲人、欧洲人、亚洲人、澳洲原住民及美拉尼西亚人之间。他们之间存在肤色差异、发型不同,无疑都是现代人走出非洲后、自旧石器时代以来演化的结果。可以肯定他们的分布不会和3万年前一样。反之,在我看来,现代人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欧亚大陆撒哈拉沙漠以北及西欧和中亚、东亚、东南亚的分布,很大程度上是新石器时代人口扩张的结果。当然,美洲人在农业发展之前就已经定居在那里了,但就如同美拉尼西亚和新几内亚的情形一样,那儿同样也有农业扩张发生。
在您看来,近来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发展是什么?
彼德·贝尔伍德:如果要谈“发展”,那真是不胜枚举。我这儿要举的只是对我来说比较感兴趣的问题:中国新石器考古的新发现,尤其是谷物(粟和稻)和家养动物(特别是猪和狗)的起源。我认为它们不仅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发展的两个紧密相连的核心要素,并将黄河和长江中、下游互相连接,向北影响到东北及内蒙古一带。
在长江流域新发现的那些饱水遗址或其他遗址都很重要。像1万年前在形态上看起来是野生粳稻的开发利用,或7000年前筑堤围护的新石器水稻田,以及后来(距今5000-4500)的良渚大型古城。长江流域这些考古遗留,不仅体现了新石器时代向南方的扩散,也包含了大量陶器装饰元素的源流、石器和玉器的切割和钻孔技术。这些技术随后来史前人口的向外迁移而流传,尤其是早期的傣族和南岛语族。在长江下游那些饱水遗址内发现有榫卯这种世界上最古老的木工技术,如田螺山、河姆渡的木工遗留,和其他地区有相似木作遗留的国家,如埃及和秘鲁相比,前者的年代要古老许多。这种技术让古人得以建造独木舟,搭载拓殖者穿越东南亚岛屿和太平洋。新石器时代的中国还是纺织技术的主要来源,正如大家所知,近年来在长江中游的东周和汉代古墓中发现了为数相当惊人的丝织品。
长江流域在新石器时代及后来兴起并发展成了一个重要焦点。与此同时,发展的黄河流域,它曾经是我们了解古代中国的最重要窗口。虽然过去认为黄河中游是东亚地区所有重要文化的源头,但现在这个说法已不再令人信服。不过,对这个区域,是不是我们今日所称中国早期文明——夏、商、周的一个特定语言和文化祖源的形成区,还可深入讨论。当然我们也了解到,现今可以探索的问题已不仅止于中国人起源这类议题了。
中国地理区域内其他方面的许多发展也是外界颇感兴趣的。诸如现代人起源(非洲说抑或从当地直立人演化的地区说?)、新疆和中亚在新石器时代及后来的关系(这涉及突厥语和吐火罗语族群)、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从安阳到秦、汉)等等。虽然我个人相信现代人是从非洲迁移出来的,但我也知道中国有些古人类学家还是强烈渴望倾向于支持本地演化的说法。我认为新疆和哈萨克斯坦(Kazakhstan)在突厥语的起源(研究)处在一个关键地位,正如台湾对南岛语及广东、广西之于傣(Tai)语一样。据我所知,这一代中国史前学者已对这些议题较上一代更感兴趣,这对未来的研究是一个好兆头。
中国考古学和您的研究有怎样的关联性?
彼德·贝尔伍德:中国是一个如此之大的国家。我们必须了解它是如何形成的,不管是经由征服抑或是从中央省份移民出来的,尤其是那些从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向四周的迁徙。这些扩张包括北向和南向,并与当地大量原住民产生融合。这些原住民在被融合之前的语言和文化特征已很难在现代中国人中找到了。当然,或许有些史前学者能观察到一点。但这些族群的许多后裔现在都居住在东南亚和太平洋,这也就是为何我们所称的中国这个地理区域对我的研究是如此的重要,尤其是目前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证据、中国全新世的新石器发展和人口的增长。
事实上,此前我已约略提及,我觉得这个重要性值得再次强调。中国可以说是世界史前史上最重要的“主角”(player)之一。为什么?因为她大,而且过去的人种相当多样化。最重要的是她有两条世界上最富饶、丰产的河流,即黄河、长江。如果你曾考察过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密西西比河或亚马逊河的周围场景,你就会理解我的意思。中国很幸运地拥有温带纬度气候、丰沛的季风雨及广阔肥沃的冲积土壤,而且它还有世界上最早的农人,甚至有些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或最稠密的新石器人口,它的重要性众所周知。
关于南岛语族的起源和扩散这个议题,您近来有什么想法?
彼德·贝尔伍德:显然,南岛语族的祖先在古代从它们的某个故乡,携带了其基因、语言、物质文化及他们特有的食物生产经济,穿越了太平洋。我从来不认为语言可以不通过人类迁徙而径自扩散。不过,我知道有很多同行特别热衷于接受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语言学家所称的“语言转换”(Language shift),是指当人们放弃自己的母语后,接受另一个外来语,这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区域化过程。在过去的500年,殖民国家强化了这方面的发展,但语言转换本身并不能解释几个大的语族,像南岛语族的分布。那些早期南岛语族人确实存在,而且他们的确经历了利用独木舟搭载的迁徙方式到达太平洋。但他们是从何处、何时以及从哪个方向迁徙来的?1978年,当我写《人类征服太平洋》这本书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并不像今天这般清楚,即使现在我还同意当年我的出版物中的大部分看法。但这些年来,对南岛语族更为深入的史前史研究,以及广泛的人类史前史研究,我逐渐又发展出了一些新看法。
在我当前思考东南亚和太平洋史前史时,中国这个地理区域较1978年已显得更为重要。当然这要归于前面提到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尤其是长江流域和华南新石器时代族群(的考古发展)。但这些早期南岛语族并非我们今天所称的“中国人”。他们不说汉语,而且也可能和黄河流域的中国文化的根基没有直接关系。距今2500-2000年前,中国拥有相当多样化的新石器和青铜时代族群。如今,这些人的后裔还存在于东南亚和大洋洲,但许多族群的大部分最终融入了现在仍在扩展的中国文化的世界中。语言学家认为,那些在东南亚和大洋洲的族群,像傣族、南亚语族、南岛语族(Austronesian)、藏缅语族(Tibeto-Burman),在某种程度上都能追溯到中国南方,他们在迁徙后都和当地原住民很明显地融合了。
提到我较关注的早期南岛语族,多年来我一直认为,南岛语族的祖先可能是稻作、甚至粟作的新石器农人,他们在距今6000-5000年前从福建来到台湾。他们在台湾发展出语言学家今日重建的“原南岛语”(Proto-Austronesian),并保持了沿海经济超过1000年,直到约4000年前迁移到巴丹群岛和菲律宾北部,携带他们传统的制造红衣陶器的技术、台湾丰田玉耳环、磨制的有肩有段石锛、栽种谷物、驯化猪和狗及发展成熟的海洋鱼捞业和造船技术等。
南岛语族的史前史太过复杂,我无法在此叙述。但重要的是要记住,他们经历了4000多年的殖民扩散历程,从一个岛屿到另一个岛屿,直到公元1200年最终经波利尼西亚中部和东部岛屿到达新西兰。就像我前面提到的,我不认同最近一些看法,即南岛语在东南亚岛屿的扩散并非人类迁徙所造成。我坚信食物生产经济和海洋知识这两者对其扩散有很大刺激因素。自然,早期拓殖者在未开发的岛屿发现了许多野生资源,尤其是海洋哺乳动物和鸟类,或许农业的重要性在这些早期殖民者生活中多少受到了影响,可能就像我们从早期毛利人(即所谓毛猎人,Moa-Hunter)那里观察到的,这种影响是暂时的。但这种情形并不能否定食物生产经济的重要性。没有这一动因,可能许多太平洋小岛长期以来都不会有人居住。
在您看来,在今天和未来,我们研究东南亚和太平洋考古时,哪些是最有趣的、且富于挑战性的?
彼德·贝尔伍德:最重要的历史或族群问题总是围绕几个主题,诸如现代人出现的时间、几个主要农业族群扩散的时间和方向,以及稍后与外界文明、宗教和贸易的接触,犹如距今2500年前的印度和中国文明。
就现代人起源这个议题,在这一区域颇受关注。考古学家面对关于现代人的标准(markers of modern humanity)问题通常持有这种看法,像石叶石器、石矛,使用赭石和纺织品及艺术表现,都普遍见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举例说,我们很难就印度尼西亚爪哇的旧石器现代人使用的旧石器来区分他们和更早的直立人的行为能力。无论如何,如今我们已较清楚地知道——在西方旧世界,即便非洲,现代人和较古老的人类行为能力不大容易有明确区分。换句话说,考古学家在解释现代人的迁徙问题时,不能忽略生物人类学和古代基因学的研究结果。
同样,我们要了解新石器时代的发展,必须注意与考古学平行的其他学科。如比较语言学,刚才提到的生物学等。对于考古学家坚称只有他们可以直接研究人类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现在有些人仍抱残守缺,恐怕不久就会发现,他们的研究忽略了古代基因、古人类学和语言学重构这些研究的热潮。
另外有个很重要的挑战,当我组织印度-太平洋史前大会时,我经常体验到一种发生在考古学界的所谓“语言独裁”(tyranny of language)。有时我们必须阅读来自不同国家出版的考古报告,而许多人使用的是超越我们阅读能力的语言。工作繁忙的考古学家不太可能流利地使用多种语言——即便有些人或许有此能力,但期待每个人都学英文或学其他几种主要语言——像中文——以便能够阅读考古报告是不公平的。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最关键的解决办法可能是使用有效的计算机翻译,将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
幸运的学生或许可以通过在国外求学的机会增强其外语能力,但这样的机会并非每人都有。况且我知道,很多人选择到国外求学后,很难在其祖国找到工作,甚至被排除了在祖国发展的机会。对这些问题并没有一个简单答案,若想增强与不同地区学者接触,并达到获取国际性知识水平的能力,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组织国际合作计划。
可否谈谈您的下一本书,即关于人类迁徙的大作?
彼德·贝尔伍德:此书是应美国威利-布莱克威尔(Wiley-Blackwell)出版社之邀而写的。所考察的是从早期人类离开非洲到现代人扩散,以及稍后全世界的食物生产经济。我认为“迁徙”是人类行为中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在其他灵长类动物中并不是如此显著——尽管我们知道一些哺乳动物、鱼或鸟类有迁徙行为。但除了那些和人类共生或家养的动物外,没有一种动物能像人类这样如此广泛的拓殖。在过去1000年来,迁徙的重要性随时间消长而变化,但它确实在人类史的某些转折关头显得格外重要。我这本书的编排将会以地理区域和年代学为基础,除了考古证据,我将尽可能提供生物学和语言学证据。人类史上有很多重要事件,像现代人扩散,其后进入东南亚,很难在考古纪录中观察到,除非像是澳大利亚这种在现代人抵达之前完全没人居住的环境。
您未来的研究主题有哪些?您的新的田野工作计划是什么?
彼德·贝尔伍德:今年(2011),我和同事欧·马克(Marc Oxenham)、你(洪晓纯)和菲利浦·派普(Philp Piper)从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获得了一大笔基金,支持我们继续从事东南亚的新石器研究——在越南南部、菲律宾北部和关岛的研究计划,目的是寻找当地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发展的证据。我们将针对越南北部和中国广西的史前墓葬及墓主的健康、型态学进行研究,也希望能在中国台湾地区甚至海南岛做些研究。
我们的目标是考察距今4000年前后广泛出现的新石器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经济、生物型态学、古代基因(如能提取到的话),甚至包括健康和人口统计学等内容。我们计划在接下来的五年持续上述研究。再以后我可能退休,去做一些比较不费劲的事了。
对那些有志于从事东南亚或太平洋考古的年轻学生,您有怎样的建议?
彼德·贝尔伍德:要从事长期的考古学研究,最好参与一个大型合作研究计划,而且这个计划能有多年的经费支持,这些支持可以资助博士后研究员(当然,现在拥有一个博士学位是考古学研究生涯或其他科学学科的首要条件),不少学生通过其博士导师协助得到这样的机会。在澳大利亚,这类研究经费来自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美国则来自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总之,我的经验仅基于澳大利亚的经历。澳大利亚所有重要的考古学研究都在大学进行。但在许多国家,政府资助的研究机构扮演重要角色,他们也提供经费,像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及中国各省区的考古研究所、台北的“中研院”、马尼拉的国家博物馆、曼谷的泰国艺术部(Thai Fine Arts Department in Bangkok)等。但我要强调的是同样的建议,即参与一个大型研究计划,而且试着去发展一个专长。这样你的专长将会得到充分的发挥!
后记
在2011年3月发行的《古物》(Antiquity)期刊中,特别开辟了一个专栏,向贝尔伍德教授表示敬意。该专栏首先陈述贝尔伍德对东南亚考古学及世界考古学的贡献,其中集结了由查尔斯·海汗(Charles F. W. Higham)、格兰厄姆·巴克(Graeme Barker)、马修·史必思(Matthew Spriggs)、帕特里克·克区(Patrick V. Kirch)等新西兰、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知名学者针对同一主题所撰写的论文。2011年这一专栏的刊出缘于2009年在越南河内召开的印度太平洋大会,其中有一特定议程,由几位代表学者组织并发表了多篇向贝尔伍德教授致敬的文章。当时发表的其中几篇文章并加上后续邀稿由《古物》(Antiquity)陆续刊出。
洪晓纯、李水城
【本文初发表于《南方文物》2011年3期;后收入《穿越古今:海外考古大家访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澎湃新闻经李水城教授授权刊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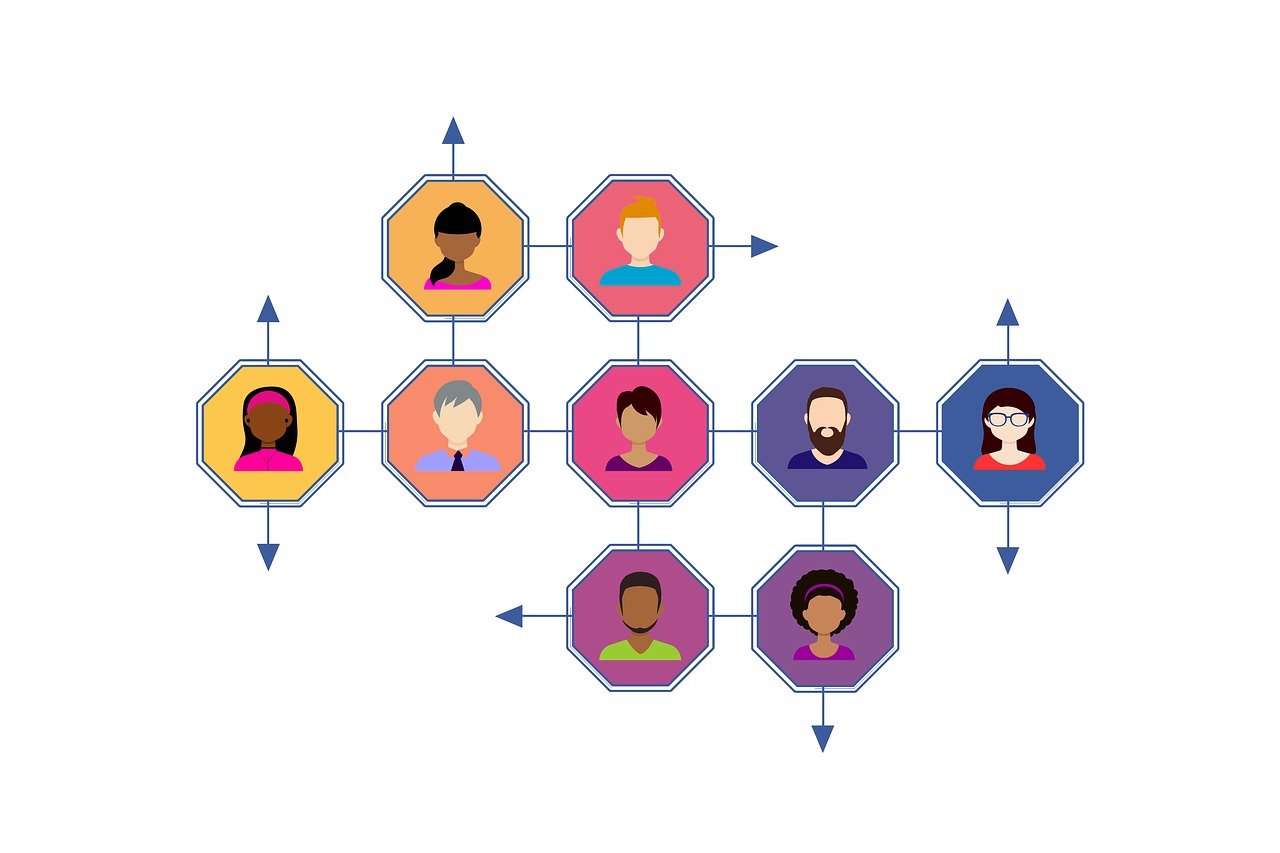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