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遗民意识总已暗示时空的消逝错置,正统的替换递嬗,后遗民则可能变本加厉,宁愿更错置那错置的时空,更追思那从来未必端正的正统。”[1]王德威在《后遗民写作》中如是说。而如果说“忘却”是以“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的方式迈向新世界的大门,那么“纪念”则是“还原历史真相而不得,终徘徊在时空余烬”的无望。由此延宕开去,倏忽千载,多少记忆在生死间蒙尘,多少逝者沦为空间与时间的“遗民”。
郑恩柏的新作《蛮与痴》正是一部遗民之书——不仅书中三部分所勾画的二十二位人物各自以不同方式回忆起的械斗往事早已沦为“遗迹”,他们所缅怀和追思的那些已逝之人已成为“遗容”,而他们自身亦无不困囿于念念时空,成为无法自拔的“遗民”——那些参差错落、混乱驳杂、真伪莫辨的记忆碎片,与蛮话人及蛮话本身形成了彼此指涉的微妙关系。与其说它们接续了苍南县江南垟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信仰,毋宁说在在撕裂、弥散了记忆自身,历史因此既是似有还无,又是无孔不入,印证了德里达的魂在诗学(hauntology):“它早已来了,却处于已来又未来的状态,虽然被遮蔽,却作为幽灵早已、一直、始终在舞台上游荡。”[2]
当械斗的血性最终坍塌为档案室的尘埃,当方言的鲜活沦为访谈的标本,《蛮与痴》恰恰以其未完成的叙事姿态,为当代文学提供了珍贵的病例切片——我们听见的不只是渔村的回声,更是整个时代嬗变的精神症候。

汪晖从鲁迅的论著中发见:“无名不仅是历史的本来状态,也蕴含着创造力和未来性……经验中埋藏着无数的、源自不同方向的、无法用‘名相’加以概括的牺牲,因此,无名者自觉名相与己无关的瞬间正是‘真实’得以显现的时刻……如果历史叙述中的有名者是记忆筛选的产物,那么无名者则是遗忘之海本身,他们尽管个性和经历各异,但不可避免地具有群体性特征,他们只是在革命、战争、灾难和巨变中才能以群体形式显形。”[29]读者大可察觉《蛮与痴》与《狂人日记》在创作地域、书名和叙事线索上的相似性,但除去作者并不认同的牵强附会的论断,我们应当找到两大著作在历史认识上的关联性:如果彼时的鲁迅将历史怪兽视作吃人的“大有”,那么《蛮与痴》则将其幻化为附身的“大无”,消逝的纸面资料、挫败的理想、不可抵达的记忆,或许与七年后的鲁迅所顿悟的“无物之阵”结成了结构性的对话。
小说多次写到这样的场景:阿妈“有何物事想逃,逃不出去”[30],早餐店主“何物也冇看到”[31],明勤感到那艘船“如此庞大,却沉默得仿佛消隐于世间”[32],陈明胜阿妈“何物也冇争来”[33],陈永坤认为“做了几年牢”罪也还不清,“有人”吞下鸬鹚囒但它“也许始终在那,从没有化开过”[34],被拐卖女人“觉得面前这些物事不晓得哪里来的”[35],离乡之人“听到空气在炸裂,可是一抬头,却连半点风声都没有”[36],计划生育出逃女人感到“声音明明顶远,又感觉顶近,越听越不真实”[37]……在他们身上,历史的无名性不仅时刻降临,成为难以言状的命数,而且当他们为之哭诉、宣泄或逃离之时,自己也同样被纳入新的无名之中,乃至延续并加剧了历史的无名,这种加剧并非“吃与被吃”的关系,而是无名自身的无限增殖,如同没有人可以仅凭坐牢免去械斗的罪过,但口述的所有人却都显得如此真诚和无罪。同样的,他们中的多数诸如早餐店主、被拐卖女人、离乡之人、东湾生意人甚至连称谓都没有的“有人”都是无名者,这群无名者埋藏着无数种表述历史的方式,但如汪晖所说,他们正是遗忘之海本身,只在械斗中才能以群体形式显形。这群“庸碌”之辈在口述中注定多多少少包装了自己再造的身份,尤其是作为受访者的角色,但在某些叙述时刻,那些在苦难乃至穷途末路的催逼下意识失去作用的时刻,他们才认识到自己和有名的世界其实是无关的,正如被拐卖女人疯癫的瞬间:
顶冇钞票的,新妇讨不起,才买伊们那些老货……一斤七两,身体健康,好生养,准定生男伢仔……统是姓陈的那些山种,讲起来好听,钞票收去给政府,呸,政府碰到伊们姓陈的还不是得叫阿翁!一张结婚证这样棺木贵……挑鸡仔也挑肥肥个,瘦叽硌陵登,养了活噶……伢仔生下来就好了,尔要伊逃伊也不逃……食我的用我的,尔阿母……铁链把我拽牢,铃铃响,铃铃响,响冇歇……[38]
此处,所有的记忆断片,那些最真实的视听印象被调动出来,揭示着她被压抑的痛苦同时,也证明历史怪兽的无名性如何让这个无名的女人成为自觉“倒带”的容器。
而对于那些“有名者”,“无名”又是何以在其身上发生作用的呢?三兄弟出海的失败固然是其最为现实的昭示,明泽的死亡更沉重地道明:无名的历史用暴力和遗忘的方式强行将“有名者”转变为“无名者”。但是,三兄弟更为隐秘的心灵世界实际上同样深锚了看待历史的方式,以至于主导了他们的动机,乃至命运。在第一部第三章开头,他们的动机便呈现为“打算用自己的方式庆贺他们堂兄的婚礼”[39];在陈明胜的转述中,明勤同样说“伊们想捞鱼来给阿胜当讨亲的礼物”,并且“讲的时候很认真”[40]。随着普通话叙事时间线的发展,读者不难察觉对象征“自由”的大海情结、证明自己并得到关注的渴望以及如《沉沦》主人公般青春期无处发泄的苦闷构成了他们出海打渔的情感动机。然而,小说在第二部第十三章的一处细节为我们提供了更为重要的线索。
老人说,海上不太平啊,以前从没有这么多古怪之事,近几年却频频发生。好像自从毛主席离世,山河湖海里的邪祟都压不住了,通通往外冒。众人悲叹,渐渐从对他人的同情转为自我哀怜,最终导致那股深邃而广袤的忧伤四处弥漫。还有许多人,再度怀想起毛主席在世的日子,继而深深陶醉在至今铭记那份恩德的满足中,徒留两个家庭暗自饮泣。……三兄弟自始至终不曾分享过这份悲哀,他们被激情包裹,已经好几次偷偷潜入那只船中,做着出海前的各项准备。[41]
面对那个如戴锦华所说已然成为“中国社会‘正常肌体’上似可彻底剔除的‘癌变’”[42]的历史,众人以哀叹或陶醉的方式,表达了一套符合中国古代社会或前革命社会运行逻辑的帝王神异观。但对三兄弟而言——这群同样经历了这段庞大的历史,甚至可能是其主力军的年轻人,却表现出极为反常的态度。是什么造成了无视?又是什么促成了“激情”?显然,上述诸多动机是难以支撑的。如果说,彼时新时期的改革举措是其时代诱因,那么这个在1980年代初尚属偏僻闭塞的弹丸之地何来春风可享?三兄弟延续老一辈的出海捕鱼方式更足以作为反驳,他们的激情必然与过去有关。众人是视其已尽而悲,而他们是因其未死而乐;或者说,是过去的幽灵用借尸还魂式的降临重演了这段“激情”和激情败亡的灾殃。这正应验了陈永坤关于明勤的叙述隐喻:“娒娒刚从腹肚里抱出,给日头吓着了,眼睛就撑不开了……讲伊那是眼皮给障眼鬼糊了,得在日头正的时候,把窗头布划一道开,眼睛也就撑开了。”[43]借用小说的话来说便是:“那时的障眼鬼离开了吗?抑或只是被他遗忘?”
所以,我们在“无名者”身上看到了历史的强制力和增殖力,而在“有名者”身上则看到其鬼魅性和召唤力,三兄弟因而在其唆使下一步步走向俄狄浦斯式的终局:命可逃乎?那么,明泽之死并非械斗所致的情节安排也便有了解答。无名历史于是既是命运催迫之鬼,又是柏拉图所谓“诗神凭附”之鬼,三兄弟的出海历险、受访者似真亦幻的记忆碎片何尝不是关于生死无常、历史错置的诗篇?
魂兮归来,书写即召魂。郑恩柏用他的笔触召唤出无数被历史怪兽“无名化”了的生命,而他不只面向过去悼亡,也面向未来悼亡,蛮话、蛮话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还有那些“错置的时空”,“从来未必端正的正统”或许也一如既往,等候历史怪兽的光临。“不知生,焉知死”宁愿转变为“不知死,焉知生”,正如彼得·布鲁克斯视叙事为死亡冲动,叙事成为预知死亡的方式,先行纪事,以俟大限[44]。
余论
当然,作为一个95后文学新生代,郑恩柏的首部作品《蛮与痴》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譬如措辞和结构稍显刻意、缺乏一定的留白等等。但难能可贵的是,在文学市场化和文学退潮近三十年后的今天,身处城市的他依然用童年的故乡和纯文学的写作姿态抵御着时代的泥沙,去书写那些即将或已然被忘却的乡土,去忠实于最真实的、最底层的生命经验。这些潮湿深处的呢喃也如黄钟大吕,向如今的文学界提出新的挑战:乡土文学该往何处去?那些乡土和乡土的遗民又该以何种方式被纪念?郑恩柏说,权且将这部作品称为“后乡土文学”吧。在“后”学盛行且蔓延的今天,我们希望乡土文学也能迎来新生。祝福并期待他的新作。
注释
1.王德威:《后遗民写作》,台北:麦田出版社,2007年,第47-49页。
2.李昀:《将-来的书写,德里达的幽灵政治学探微》,载《文艺理论研究》2021年第1期,第189-197页。
3.路杨:《上海的声景:现代作家的都市听觉实践》,载《文化研究》2018年第1期,第29-50页。
4.崔莹:《王德威评莫言阎连科王安忆》,腾讯文化2015年03月06日,参见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310-83211.shtml。
5.郑恩柏:《蛮与痴》,上海:文汇出版社,2025年,第14页。
6.郑恩柏:《蛮与痴》,上海:文汇出版社,2025年,第370-371页。
7.郑恩柏:《蛮与痴》,上海:文汇出版社,2025年,第368页。
8.郑恩柏:《蛮与痴》,上海:文汇出版社,2025年,第53-55页。
9.郑恩柏:《蛮与痴》,上海:文汇出版社,2025年,第356-357页。
10.郑恩柏:《蛮与痴》,上海:文汇出版社,2025年,第195-199页。
11.【法】保罗·利科:《从文本到行动》,夏小燕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9页。
12.肖文婷:《保罗·利科的“叙事阐释学”与中国文学阐释学的理论构建》,载《中国美学》2024年第1期,第36-48页。
13.郑恩柏:《蛮与痴》,上海:文汇出版社,2025年,第349页。
14.史铁生:《务虚笔记》,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6页。
15.郑恩柏:《蛮与痴》,上海:文汇出版社,2025年,第141页。
16.郑恩柏:《蛮与痴》,上海:文汇出版社,2025年,第366页。
17.郑恩柏:《蛮与痴》,上海:文汇出版社,2025年,第173页。
18.郑恩柏:《蛮与痴》,上海:文汇出版社,2025年,第177-178页。
19.郑恩柏:《蛮与痴》,上海:文汇出版社,2025年,第285-299页。
20.郑恩柏:《蛮与痴》,上海:文汇出版社,2025年,第18页。
21.郑恩柏:《蛮与痴》,上海:文汇出版社,2025年,第276-277页。
22.郑恩柏:《蛮与痴》,上海:文汇出版社,2025年,第253页。
23.赵刚:《精神危机是如何克服的?——陈映真的1980年代》,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8期,第77-130页。
24.郑恩柏:《蛮与痴》,上海:文汇出版社,2025年,第331-332页。
25.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页。
26.王德威:《历史与怪兽》,台北:麦田出版社,2011年,第10页。
27.参见余炳辉:《苍南县江南三区宗族械斗的起因和衰落》,载《末定稿》1986年第3期。
28.参见刘小京:《现代宗族械斗问题研究——以苍南县江南地区为个案》,载《中国农村观察》1993年第5期,第44-56页。
29.汪晖:《历史幽灵学与现代中国的上古史——古史/故事新辨(上)》,载《文史哲》2023年第1期,第5-41页。
30.郑恩柏:《蛮与痴》,上海:文汇出版社,2025年,第15页。
31.郑恩柏:《蛮与痴》,上海:文汇出版社,2025年,第21页。
32.郑恩柏:《蛮与痴》,上海:文汇出版社,2025年,第26页。
33.郑恩柏:《蛮与痴》,上海:文汇出版社,2025年,第36页。
34.郑恩柏:《蛮与痴》,上海:文汇出版社,2025年,第208页。
35.郑恩柏:《蛮与痴》,上海:文汇出版社,2025年,第218页。
36.郑恩柏:《蛮与痴》,上海:文汇出版社,2025年,第251页。
37.郑恩柏:《蛮与痴》,上海:文汇出版社,2025年,第270页。
38.郑恩柏:《蛮与痴》,上海:文汇出版社,2025年,第216-217页。
39.郑恩柏:《蛮与痴》,上海:文汇出版社,2025年,第11页。
40.郑恩柏:《蛮与痴》,上海:文汇出版社,2025年,第78页。
41.郑恩柏:《蛮与痴》,上海:文汇出版社,2025年,第275页。
42.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2-43页。
43.郑恩柏:《蛮与痴》,上海:文汇出版社,2025年,第74-75页。
44.参见彼得·布鲁克斯(Peter Brooks)的讨论,Reading for the Plot: Design and Intention in Narrativ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2。

《蛮与痴》,郑恩柏/著,文汇出版社·惊奇,2025年1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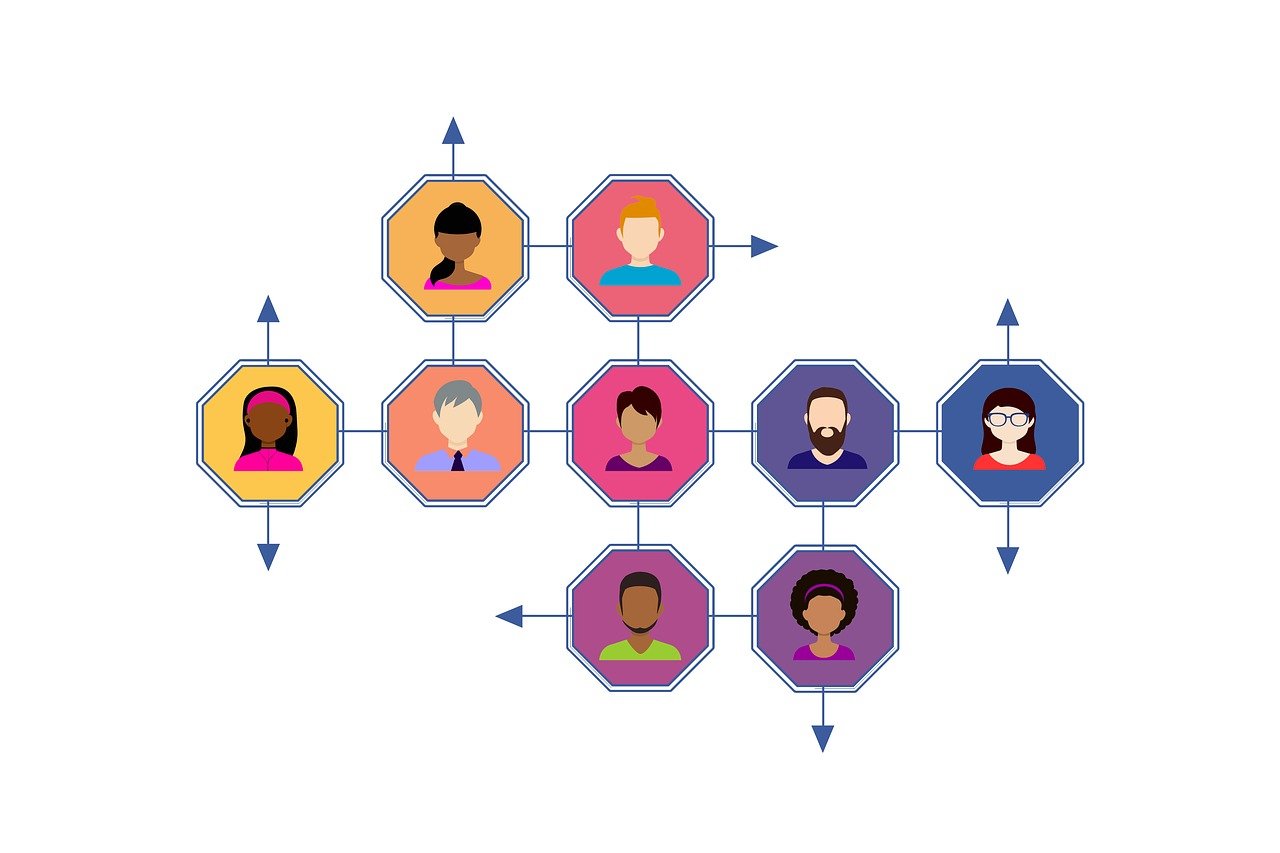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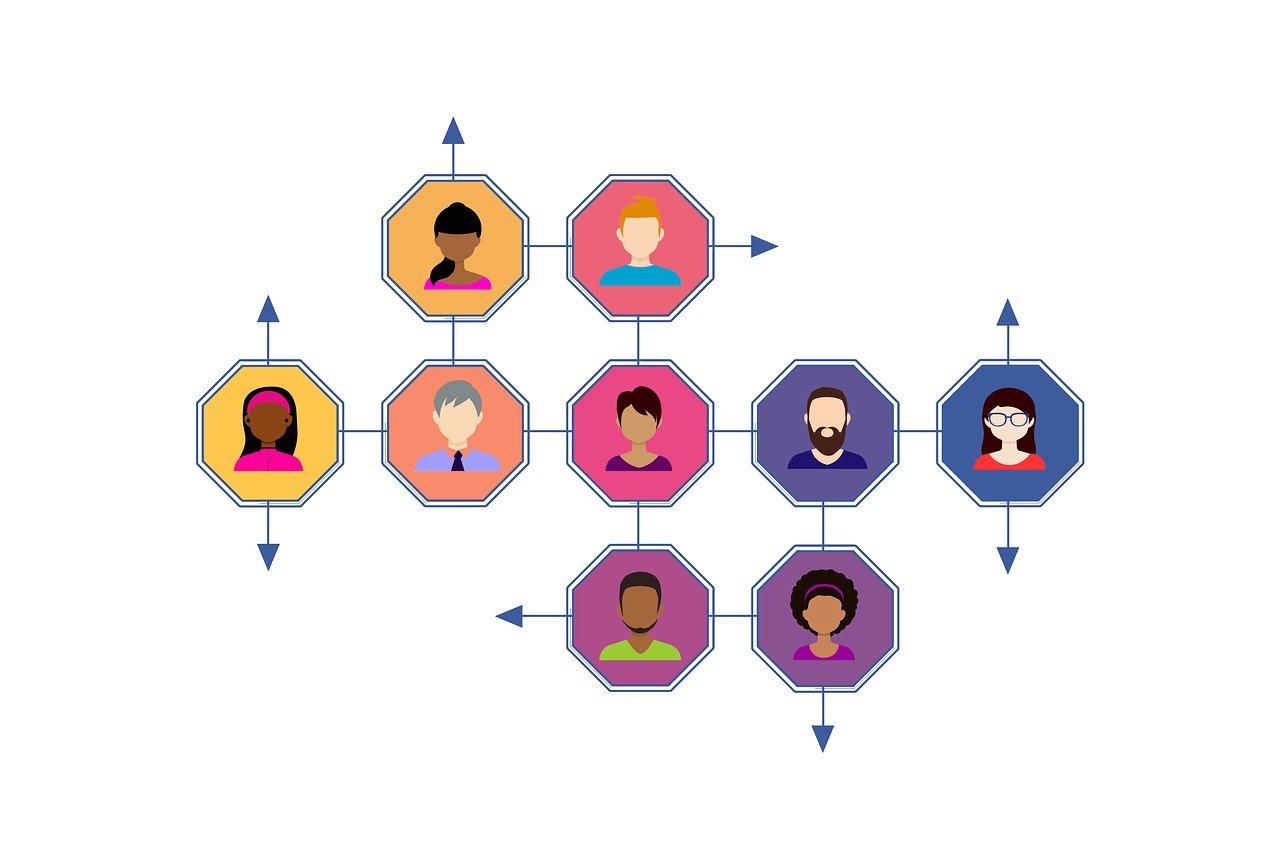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