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乌尔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城邦,在公元前2800年到公元前2000年曾是贸易和文明的中心。《乌尔:月神之城》一书着眼于乌尔的过去,不仅介绍了这座古代城市及其几千年来的变迁,还考察了近代的考古学解释。该研究从19世纪探险家寻找乌尔城开始,继而详细讨论了考古学家伦纳德•伍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重要考古发现。以这些发现为框架,作者利用环境、历史和考古研究的最新证据,探讨了乌尔从公元前五千纪欧贝德时期直至亚历山大去世的历史。本文为该书第十章《死亡与重生》,澎湃新闻经商务印书馆授权发布。
公元前539年,居鲁士征服巴比伦,结束了新巴比伦帝国的统治。在乌尔发现了居鲁士的砖块,由于他在胜利的第二年就去世了,所以肯定是在巴比伦灭亡后不久就在这里开始了建设。我们在进入圣域最南边的大门——例如伍利称为居鲁士门(Cyrus gate)的地方——发现了居鲁士的砖块。他修补了圣域的墙壁,整修了恩农玛,拆掉尼布甲尼撒增加的侧厅,但留下了中心部分存在近2000年的五个房间。这项工程可能由居鲁士的继任者冈比西斯(Cambyses)完成,他用完了为居鲁士修复计划制作的砖块。居鲁士的殷勤并不总有助益,塔庙本身的用途似乎被彻底改变了,平台西北部建造了劣质的工场、窑炉和房屋。很难知道波斯统治者还做了什么,因为许多土丘的顶部已经遭到侵蚀毁坏。
侵蚀作用也破坏了该城大部分建筑的上层,不过波斯时期的许多泥板留了下来,表明乌尔在波斯君主的统治下恢复了繁荣。最近发现的泥板年代更晚,到了亚历山大统治的第12年。有许多墓葬暴露在地表,已经被彻底盗掘。少数保存较好的情况,比如上一章谈到的NH地区,在房屋零星的遗迹地下发现了墓葬。要确定这些空空的墓葬的年代非常困难,因为其中一些埋葬方式在新巴比伦和波斯时期都很常见。不过,房屋地板下的砖砌拱顶——最早见于乌尔第三时期——变得越来越少见,到新巴比伦时期几乎已经消失。而一端平直、一端呈圆形的泥棺只见于上部的地层。有两座墓葬中的泥棺内放着铜制的内棺,用铜支架固定在一起。直到送去清洁后,才露出上面迷人的动物和花卉装饰。

波斯棺材上的装饰,玛丽·谢弗森绘制
当幼发拉底河的河道东移,乌尔失去了水源,城市的末日似乎已经到来。这种转变看起来是逐渐发生的,因为在环绕乌尔城东侧的大运河河床中发现了两座波斯人的墓葬,表明即便在运河干涸之后,这座城市仍在竭力生存。可以想象,随着水资源日益稀缺,农业生产停止,人口逐渐减少。我们不知道这些人去了哪里,但事实证明,干旱成了一件因祸得福的事——至少对考古学家来说是这样,因为它让这座空城被封存在一片荒芜的沙地中,除了贝都因人,1500多年来无人问津。直到19世纪,外来者才开始重新探索这一地区。自从1922年伍利开始他的发掘工作,乌尔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重生,因为这座城市的历史被揭示,旅行者又开始造访这里。随着伍利在大众杂志上发表大量他最具轰动性发现的照片,乌尔的名声也传播开来。然后,如第一章所述,阿加莎·克里斯蒂出版了她的《美索不达米亚谋杀案》,人们普遍认为这本书是基于她对乌尔的造访写成的——最初是作为伍利的客人,后来成了马克斯·马洛温的妻子,后者是为伍利服务时间最长的助手。所有这些宣传增强了公众的兴趣,当大英博物馆展出一些宏伟的发现时,这种兴趣得到了进一步提高。1934年,在伍利最后一季的工作结束后,大英博物馆没有继续在乌尔的考古工作,尽管伍利直到去世都一直在出版著作。后来,伊拉克考古学家进行了一些修复工作。
接下来,该遗址以一种令人难以接受的方式引起了公众注意。1991年和2003年的两次海湾战争造成的人类悲剧,以及对伊拉克无法替代的遗产的破坏,都被详细地记录下来。1990年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后,伊拉克遭到了惩罚性制裁,小农和劳工陷入了真正的贫困,有时甚至无法养家糊口。1991年武装入侵后,南部什叶派的起义失败,这导致了萨达姆的残酷镇压和更大程度的灾难。起义还导致了对13个省级博物馆的大量抢劫事件,战利品很快被偷运出国并变卖,有的卖了一大笔钱。这种快速和相对容易的赚钱养家糊口的机会,致使许多农民到当地的考古遗址挖掘任何可以出售的东西。由于伊拉克文物部门日益缺乏政府资助,几乎没有警卫在场保护这些遗址,劫掠在两次海湾战争之间就已经开始,持续了15年甚至更长时间。抢劫成为一门生意,一帮持枪和铁锹的抢夺者会赶走所有的守卫,他们来到遗址,极尽毁坏之能事。
第二次海湾战争中最受人瞩目的抢劫事件发生在2003年巴格达的国家博物馆。尽管许多人一再要求国防部和五角大楼在入侵之前及期间保护博物馆,抢劫似乎未受限制地持续了三天,留下了满目疮痍的景象。目前仍不清楚到底有多少文物被盗,因为很多还在等待入藏,所以尚未加入博物馆的库存清单,不过总数可能高达1.5万件。此外,办公室也遭到故意破坏,有人撞开了门,撕毁柜子里的文件,将卡片索引扔在地上,然后拿走了一切能够带走的东西。遮蔽安全库房入口的墙壁遭到破坏,许多物品被盗,包括存放在那里的大部分滚筒印章。幸运的是,很多最具价值的物品——包括乌尔王室墓葬的大部分物品——已经在遭到侵略前转移至国家银行的保险库。但甚至在那里也不安全,由于供水系统遭到严重破坏,这些物品被渗入保险库和存放物品的大箱子里的污水淹没。一些著名的尼姆鲁德(Nimrud)象牙被认为已经损坏,无法修复。似乎有不同的团伙抢劫博物馆。其中一群人见多识广,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可能是根据指示进行盗窃。另一群人则没有那么讲究,拿走了他们能找到的任何文物,包括博物馆商店里的复制品。还有人拿走了所有他们能拿的东西,包括办公设备和灯具。一份包含四五十件最重要的失踪文物的清单很快被整理出来,人们集中精力找回这些文物。这项任务主要落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马修·博格达诺斯上校(Colonel Matthew Bogdanos)身上,他对自己的工作做了非常精彩的描述。现在看来已经找回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被盗物品——有些由巴格达人送回,他们在抢劫后将这些物品带回自己家中保管;有些是博格达诺斯追踪到的;有些被世界各地的海关官员查获。乌尔的重要发现没有丢失。
入侵之后,盟国才意识到造成的损害,并开始计划赔偿。必须记住的是,自1990年入侵科威特以来,伊拉克一直受到制裁,这意味着它与外部世界几乎所有的联系都被切断了。再也买不到书籍和期刊,互联网也无法使用。伊拉克的学术界无法与国外的同行保持联系,也没有新的思想或者设备进入这个国家,这让学者在许多方面落后时代20年。因此,伊拉克对人才培养甚至基本设备的需求非常迫切。破坏并不限于传统的部分,图书馆和大学也遭到洗劫,许多无价的书籍和文献丢失,萨迈拉(Samarra)的玛尔威亚(Malwiya)宣礼塔等历史建筑也遭到肆意破坏。
盟国采取了各种措施来改善这种状况。意大利人为巴格达的国家博物馆提供并配置了一个新的文物保护实验室,还提供了一些基本的文物保护培训;意大利人、波兰人和德国人开始培训和装备一支新的遗址警卫队,以试图阻止对遗址的掠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对这些工作进行了协调;意大利宪兵队开始建立国家博物馆文物的计算机数据库,列出已知被盗的文物清单;美国人、德国人和英国人也提供了培训,特别是在文物保护、遗产管理和计算机技术方面。大英博物馆计划带一个保护人员小组到巴格达继续培训,但由于安全状况恶化不得不取消。其中一些培训活动仍在继续,特别是在库尔德斯坦(Kurdistan),但安全状况仍然阻碍了在南部的大规模工作。很多规模较小的组织,如英国伊拉克考古学校(British School of Archaeology in Iraq)——现为英国伊拉克研究所(British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Iraq)——也尝试提供书籍、器械和培训方面的帮助。一些国家,特别是日本也尽力提供新的设备,包括为博物馆提供新的箱子、为他们的图书馆提供新的书籍和计算机设备。
2005年和2007年,时任大英博物馆古代近东部管理员的约翰·柯蒂斯博士(Dr John Curtis)对巴比伦的军事破坏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并对乌尔的受损情况进行了部分勘测。乌尔的情况没有受到巨大损害的巴比伦那么糟糕。1991年之前的某个时候,伊拉克军方在乌尔附近建立了名为塔利尔(Tallil)的重要军事空军基地。战斗机起飞、重型卡车和机械的轰鸣声都震动了古老的建筑——这些建筑已经在一些情况下因使用现代材料进行不适当的修复而被破坏。1991年美国的一次空袭对塔庙造成了更为直接的毁坏,这次空袭据说是为了反击基地的防空火力——炮火击中了一架美国军用机。塔庙的东南立面留下了子弹孔、炮弹孔和弹片孔;营地被美国人接管后还产生了进一步的破坏,他们用铁丝网将整个考古遗址围了起来,这至少保护了遗址不被掠夺。但另一方面,基地内还进行了一些不适当的建设,比如停车场和辅助建筑。
美国人造成的最严重的破坏,是他们在乌尔城外基本未开发的、被称为迪克迪卡的地方修建了一个名为访客管制中心(Visitor Control Centre)的大型防御性入口。为减少破坏,这个大门现在已经被拆除。2008年,叛乱分子向基地发射的火箭弹落在了公元前二千纪早期被称为AH遗址的住宅区附近,造成了更多的问题。美国人最终在2011年撤出了基地;现在这里被称为伊玛目阿里基地(Imam Ali base),并再次由伊拉克军队使用。
本书试图描绘乌尔城的命运,从公元前六千纪它作为波斯湾顶端广阔沼泽中的小村庄开始,然后跟随它的发展,先是在公元前三千纪中期成为小城邦中心的城镇,接着在公元前三千纪末成为乌尔第三帝国的中心城市。公元前1800年左右,这座城市遭到巴比伦的萨姆苏伊鲁破坏,但在加喜特国王的统治下逐渐恢复了活力,成为地方首府和宗教中心,而在亚述和后来的新巴比伦国王统治时期似乎也一直保有这一地位。其中的一位国王那波尼德斯特别崇拜这座城市的守护神月神辛,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波斯征服者似乎也承认了乌尔的特殊地位,但当幼发拉底河向东流向新的河道,乌尔失去了水源,也意味着这座城市的终结。
在乌尔及附近地区,还有很多东西有待发现,很多工作需要进行。我们对乌尔周围可能存在的小的定居点知之甚少。最近,我们在乌尔附近一个被称为开伯尔丘(Tell Khaiber)的遗址展开了新的工作,该遗址有特殊的用途,包含一个大型行政管理建筑,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千纪早期。英国的一个考察队正在进行这项工作,同时意大利团队也在对该城市的周边环境进行空中勘察。由于大英博物馆和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雄心勃勃的项目——旨在将现有关于发掘和发现的全部信息数字化,新的研究很快就可以在网上进行。随着工作的进展,他们希望伊拉克博物馆也能参与进来;这将首次使有关该遗址的所有信息可以在同一个地方获得。
海湾战争以后,当伊拉克稳定下来,乌尔的未来似乎可能获得另一种生命——不仅仅在数字化方面,而是作为国家的骄傲,以及过去7000年在那里生活和工作的各种各样的人不朽成就的象征。为实现这一目标,伊拉克考古学家正在乌尔工作,进行一定的复原和整修,同时筹备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将乌尔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以承认它独特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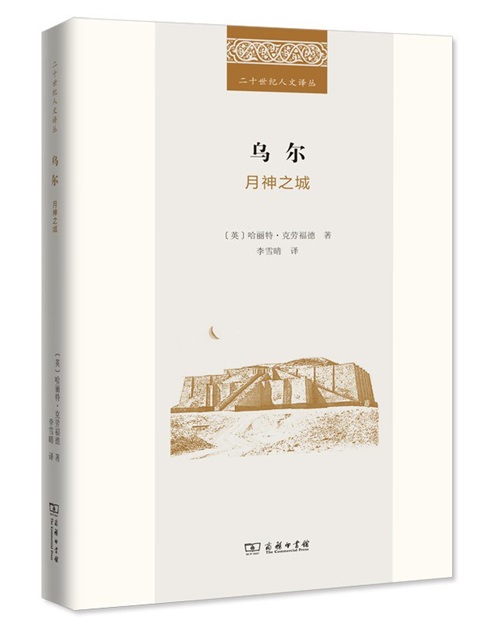
《乌尔:月神之城》,[英]哈丽特·克劳福德著,李雪晴译,商务印书馆2024年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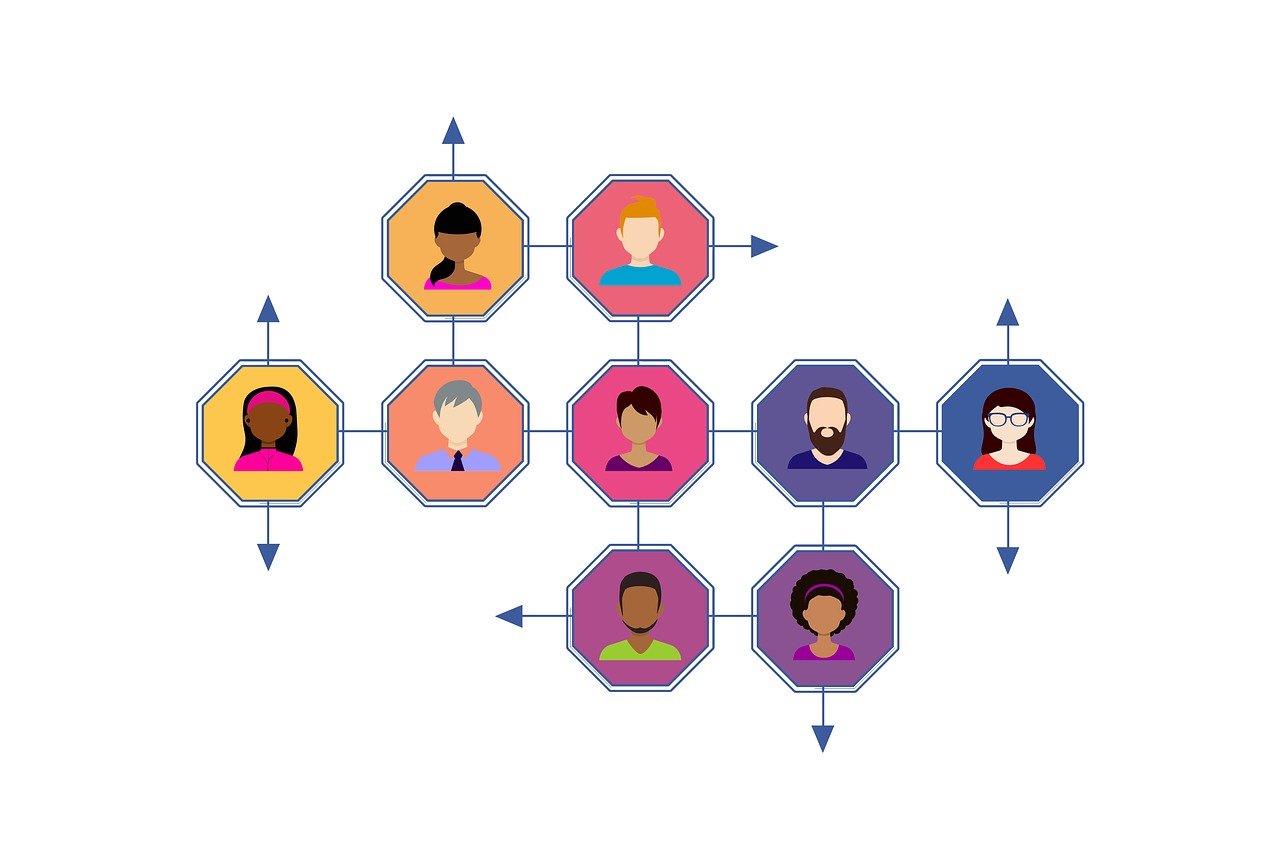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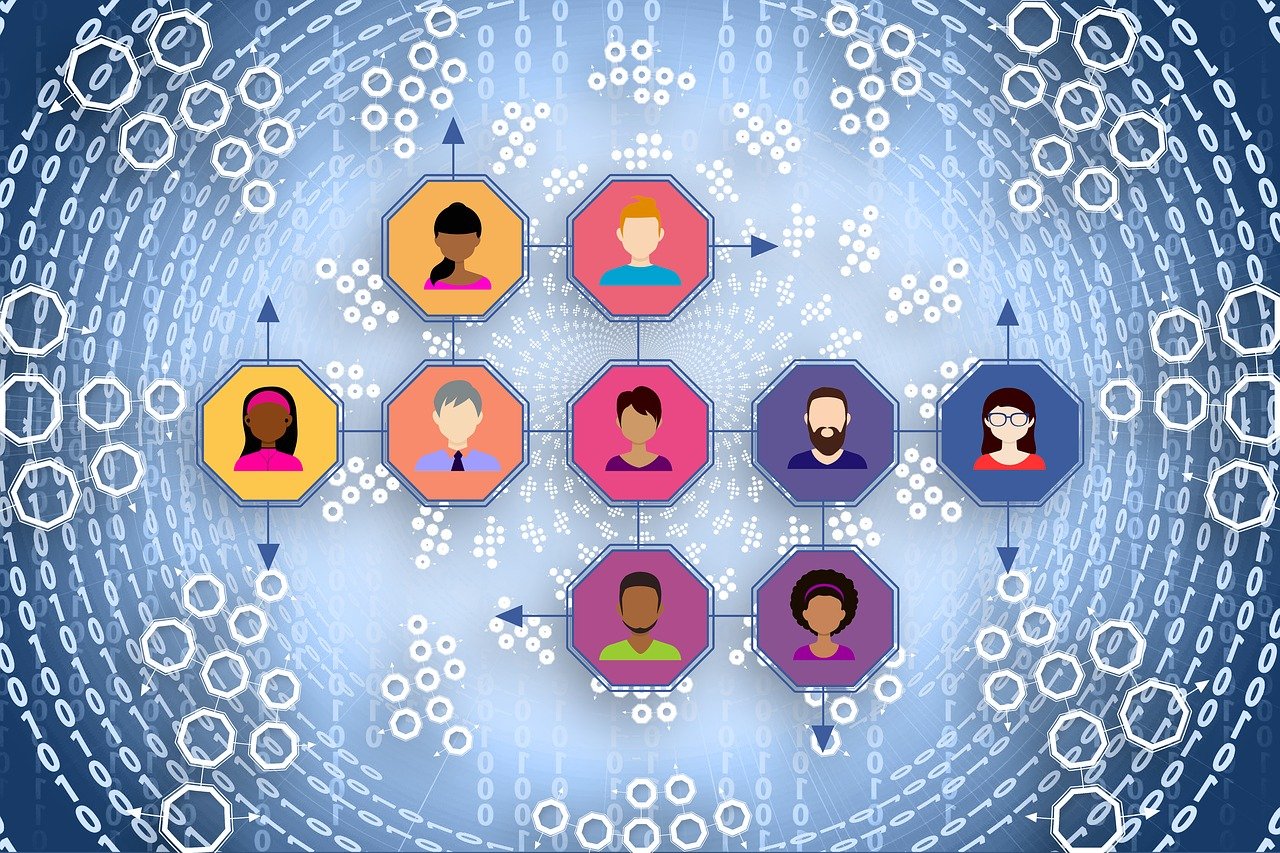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