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刚过完情人节,一场被情歌填满的音乐剧明星音乐会在上海文化广场首演。希西莉亚・卡拉与达米安・萨格,用一连串精心的编排与演绎,消除了我们陶醉于安逸中的勇气。不得不重新质问——爱,究竟是什么?
2001年,16岁的希西莉亚・卡拉与19岁的达米安・萨格共同主演了法语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首演版。正值青春年少,他们复原了莎翁经典戏剧中的“纯净之爱”①。演出大获成功后,罗朱的形象也深深印刻在两位演员的身上。

希西莉亚・卡拉与达米安・萨格音乐会海报
24年后,历经时代流转,希与达都站在了日落黄昏的人生路口,重新回看黎明破晓的悸动情境,除了怀念感动,还充斥着更多对过往经历的思考。因此,整场音乐会脱离了抒情怀旧的熟悉氛围,两人带着各自的人生幡悟,以情歌的形式,与我们一起讨论关于爱的一切。
无论《梁祝》还是《罗朱》,经典爱情题材中都有关于“纯净之爱”的呼唤。在古代封建社会婚姻制度的钳制下,爱很难不受干扰。包办婚姻、门当户对、媒妁之言的出现,都在使爱不再纯净。《罗朱》等作品就在强调,阶级、门第、族群等外界的干扰,都在侵蚀爱情纯净的基底,迫使人走向悲剧结局。而两颗纯净心灵间的爱,本就是人间真情之所在,它是人性本真中幻化而来的美。珍惜这份至美的真情,是人生意义的体现。
《罗朱》故事为个人精神境界的提升,提供了想象的舞台。“我怕”②“阳台”“朱丽叶之死”等出自音乐剧《罗朱》的经典唱段,都在强调对“纯净之爱”难能可贵一面的描画,给人以应该珍视之的憧憬。爱,所具备的永恒性,在《罗朱》的不断上演中得到充分诠释。如今的我们,都会以此来幻想爱情最好的模样。
但回到现实当下,“纯净之爱”的想象,不得不被惊醒。一首“爱情快餐的时代”点明了爱情正在当下面临的境地,一时的兴致,一时的满足,与理想中的永恒、纯净之爱形成对立。
音乐会的场景被设置在现代人常去的音乐酒吧,希与达以陌生人的姿态在酒吧偶遇。开场的两首歌(“总有一天”“我静静跳着舞”),都在交代两人已过了年少懵懂的年纪,他们的人生履历中早已刻上因爱而生的伤痕。这时的他们,理应少了冲动,多些慎重。可恰恰在四目相对间,冲动再次上演。他们会再次坠入爱河吗?或再次收获伤痛吗?
这一场景设置把两人身上具备的戏剧性色彩激发出来。幻想与记忆中的罗朱式纯爱,与现实世界里的快餐化恋爱观并置,对照出了熟悉与陌生、间离与想象共存的人物形态。两位音乐剧明星在这场专属于他们的音乐会上,展现出一种抽离自我的状态,以陌生感引领观众参与他们发起的对话,一起讨论爱的矛盾性。
这种将布莱希特陌生化表演理念,应用于明星个人演唱会的做法实属罕见,且大胆。
我们熟悉的情歌中,有太多是经历过痛楚之后的倾诉。比如心如刀割,原来你什么都不要。即使在梦醒时分,后来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也会娓娓叹息可惜不是你。我们不禁要问,爱中的苦痛始终都在,可为何爱并没有消失,这些痛心的情歌依然在唱。
情歌来自一种感悟,它强调情绪的抒发,但不容忽视的,还有对自我情感的反思。音乐会中,希与达的人物设定从相视到倾心,进而两人步入暧昧并直至演出结束。作品在这里,更符合契诃夫静态戏剧中“情绪的潜流”③,即整个舞台的动力不来自传统戏剧中的情节动力,而是由情绪在推动。情绪这一潜伏性的动力,在戏剧中并不如情节来得显而易见,但在情歌的作用下,更易显现。因此,在一个静态的场景下,两个人物之间的互动,依然有着跌宕起伏的戏剧性态势。而在情歌渲染下的情绪潜流中,许多曾不被我们关注的思想话题袒露而出,被更多人看见。
比如,纯净之爱与欲望的关联性。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纯净之爱,到了叔本华或心理学层面,都与欲望脱不开关系。纯净之爱的永恒性,其实建立在生理欲望的即时性之上。哲学与科学的进步,揭露了人本性中更具事实意味的一面。欲望就是事实,它不崇高的特征,对文学中描绘的崇高之爱是一种冲击。因此在听到“爱情快餐的时代”后,再听《罗朱》金曲便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在电影金曲“慢慢落下”“繁星之城”中,都出现了个体在情感中的自我认知。当个体与个体进入亲密关系,个体间的私密空间被打破,或者说两个个体共处一个亲密空间,一种自我审视的冲动出现。
我们常常在情歌中看到,一方自觉不配拥有这段感情,或自觉不如他人的自卑感,就在这种自我审视中显现。歌曲“一些蠢话”中,情话被自视为傻话,情话又被自我要求以委婉的方式表达,都体现了自我审视下的自谦。而到了“感觉美妙”,一个自大、自以为是的自我亦在情绪的潜流中袒露出来。个体将自我放大到难以知足的地步,永不满足就成了理所当然的诉求。但紧接着,“一些美好”又在强调苦中寻乐的知足感……

节目单
在一首接一首的情歌里,不同的自我形态逐一揭露,并形成了从自卑、自谦,到自足、自大,不知足、不满足的转变。一段感情中的那些创伤,似乎就来自这些自我认知之中。
那些自大、自恋的狂妄情绪,在戒不掉的欲望指示下,把爱变成了掌控一切的力量。受控与施控之间,同样能把两人的相处之道变得妙不可言(“小姐”“跟随你的脚步”)。转瞬在爱里越陷越深,“我为她而活”的虽然誓言震撼人心,而这句誓词又裸露了爱本身的神圣威权。对很多人来说,爱就像上苍上帝,不可逾越。到了中文情歌“默”中,那句“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不还手,不放手”,再到“为何爱判处众生孤寂,挣不脱,逃不过”,每一句都尽显人类在爱的威权面前,无能为力。可有意思的是,再下一首“重写命运”中,又出现了一段向命中注定发起反抗的精神。
每一段情歌里,爱都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价值,或被崇尚,或被祛魅。而这种对爱情二元性的不同解读,正是促成浪漫主义个体创造力的支撑。
音乐会最后并没有对爱做任何价值判决,而是把我们的目光转向全世界。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爱都被认为是二元性的,是浪漫主义的源泉,是对启蒙理性的反抗。爱既存在于瞬间,又代表着永恒。“月亮代表我的心”在进行曲式的编曲下,唱出了永动的气势;终曲“爱的礼赞”,则带着任性的语气,发出对爱的赞颂。
虽然整场演出被定义为音乐会,但从编排演绎、场景结构,到对情绪潜流的应用,以及主题“爱”二元性的讨论都显示出极强的戏剧性特征。它和许多点唱机音乐剧一样,音乐取自流行歌曲或音乐剧歌曲。不同的是,这里的戏剧结构并不是一个完整故事,而只是一个可以发生爱、讨论爱的场景。但这种建立在场景之上的音乐剧,又很符合概念音乐剧的逻辑。因此,这场音乐会更像是一场概念式的点唱机音乐剧。这种定义会让我联想到1980年在外外百老汇(Off-Off Broadway)上演的音乐剧《结婚未满》(Marry Me a Little),同样以一连串已有的音乐剧歌曲串联,讨论关于爱的话题。
注释:
①纯净之爱:参考胡德才著.叩戏剧之门:戏剧十六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174;
②文中斜体字代表音乐会中所唱歌曲;
③情绪的潜流:参考彭涛.“气氛美学”视域下契诃夫戏剧的“情绪的潜流”[J].戏剧,2024年,(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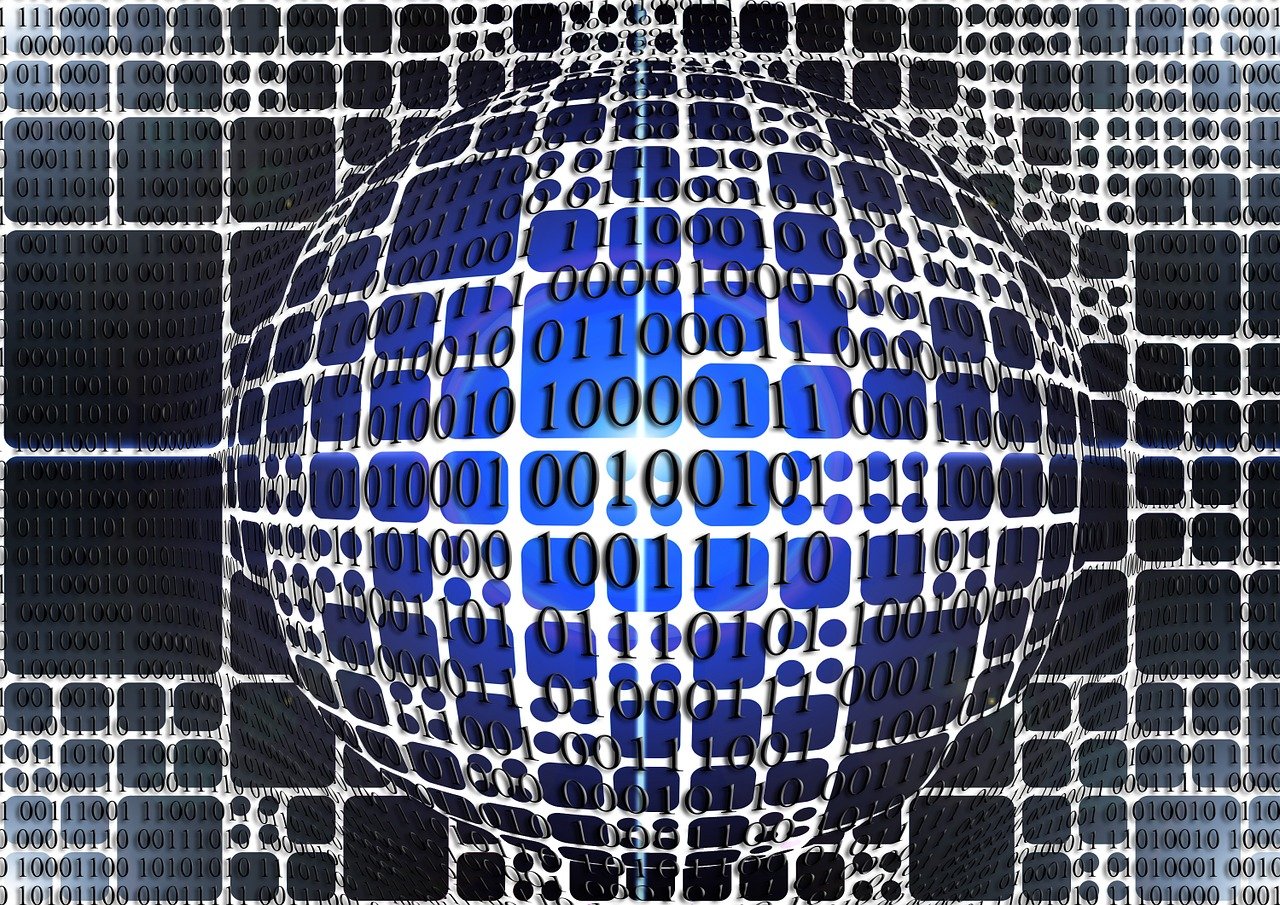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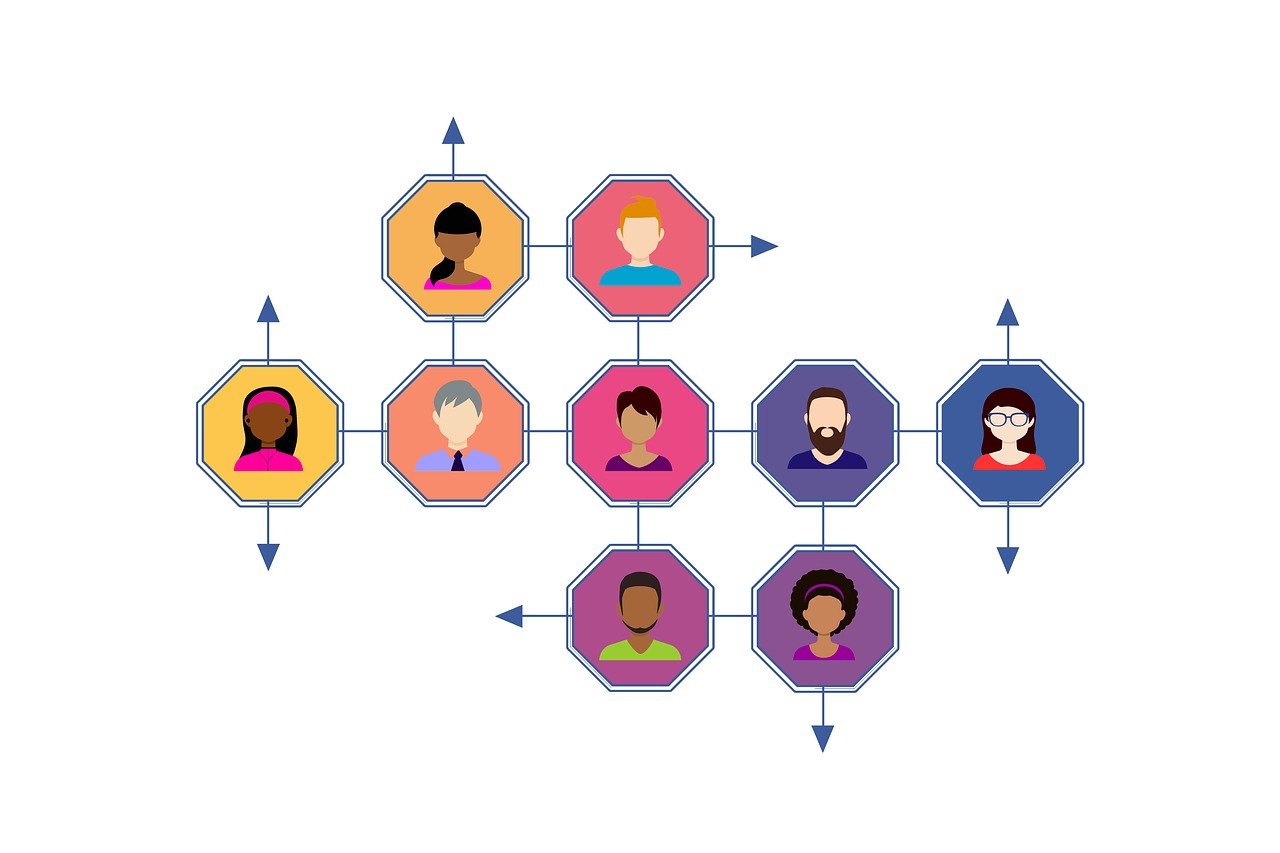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